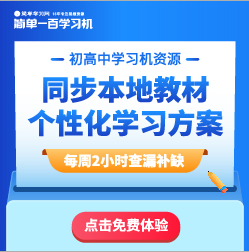八
第二天醒来,已是太阳一竿子高了。
智广随邓明三回区公所吃了早饭,就去找宋明通,向他报告昨晚从“宪兵工作队”哨兵那里听来的情况。
宋明通说:“看来昨晚那顿宴会是个关键,必须打听清楚昨晚队长和那过路干部谈判的结果。”
智广心想,此事只有找三姑娘打听,别处无门可人。自己若去找三姑娘既不方便,又难免引人注意,一个小小年纪的学生找妓院的姑娘干什么,正这时,邓明三打发人来喊宋明通,他就又和宋明通一块到了区公所。
邓明三找宋明通是布置为金队长备车的事。交代完了,宋明通就去忙活。智广想出个点子,要邓明三去召唤三姑娘。
“三叔,你为金队长热心备车,可这小子在暗地给你拆台,你听说没有?”
“没有哇,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他打我什么主意?”
“我听他那站岗的说,昨晚摆宴是跟那个八路干部讲条件。”
“这我知道。”
“什么条件你知道吗?”
“听说要是那个降了,给他个官做。”
“什么官?这里一个萝卜一个坑全摆满了,总得拔一个再按下一个对不?你知道拔哪个坑吗?”
“哪个?”
“就拔你,他们站岗的对我说的。官小了人家不动心,官大了拔不动,就你这区长,名份不小,势力不大。答应那人要投降,叫他当区长。”
邓明三一听,立刻七窍冒烟,大骂了起来,说:“我做买卖还没这么赔过。弄了个汉奸帽子戴上,本还没收回来,就要撤我!我跟他拼了。这话靠实不靠实?”
智广说:“靠实不靠实我也不知道,反正无风不起浪。昨晚不是三姑娘伺候的饭局吗,干啥不找她来问问?”邓明三一叠声地叫人去喊三姑娘,外边答应着就有人去了。邓明三坐在炕上生闷气,刘四爷挑帘走了进来。
刘四爷看看智广,对邓明三小声说:“我要走了,你还有啥吩咐的,叫大侄子出去躲躲?”
邓明三说:“他是那边的人,也不必背他了。你把这两集收的税钱交给抗日区长,说这是我们代收的,不敢留下。另外那二百,是我个人送的慰问品,请八路同志赏脸收下,只要给我条后路,我决不干‘剿共班’那样丧天良的事……”
正说着,外边喊三姑娘来了。邓明三就住了嘴。
三姑娘睡眼惺松,披散着头发,似乎比昨天老了十年。一进门先打哈欠,懒洋洋地说:“刚给上眼,你又叫魂。”
邓明三没好气地说:“昨晚上卖了力气了,没少得赏吧?”
三姑娘似笑不笑地说:“你又不赎我从良,还不叫我做生意,我怎么混世?”
“混世的才要讲个良心义气。”
“我哪点没有义气?”
智广冲三姑娘送个眼色,笑笑说:“三姑娘别当真,我三叔是心里着急。他想知道金队长昨晚宴客的情形。”
“有啥说啥,干吗拍桌子吓耗子的。”
邓明三问:“昨晚是请那个八路干部吗?”
三姑娘说:“干部不干部咱不知道,反正穿的是八路军的破军装。
“金队长说啥哩?”
“他光叫我劝酒布菜,到说正事时候就把我支出去,叫我到他跟班的住的屋里去歇着了。”
智广问:“这么说你啥都没听见?”
三姑娘说:“中间隔着半个院子,那些小光棍见了我又嬉皮笑脸地光打哈哈,能听见啥?”
智广问:“一句也没听到?”
三姑娘说:“跟班的有两人留在上房听使唤,他们溜下来歇腿,从他们嘴里听到了一星半点。”
邓明三急问:“听到啥你可快说呀!”
“他们夸那个八路是硬汉子。”
邓明三问:“怎么硬法?”
三姑娘想一句说一句:“说金队长说,他们已经查出来这人是个大干部,决不会放他了。前些天给他出了假殡,八路知道他已死去,也不会再救他来。当前就两条路。硬顶下去,决不让他过了这个年;表示合作,想当官给官做,不想当官给他一笔钱,送他去大地方享福。”
邓明三问:“许他什么官?”
智广使个眼色说:“是叫他当区长,替我三叔吗?”
三姑娘说:“人家金队长说,想当区长就当区长,想当队长就当队长,想顶哪个角就叫那个角让位。有皇军作主。”
邓明三忙问:“那人说要干啥?”
三姑娘说:“硬就硬在这里,人家一个字不吐,连大气都没出。金队长没办法,就叫人拿了一套新棉裤棉袄来,对他说,你不愿说话也行,自己把这衣裳换上,就算讲和了。你要自己不穿,年初一我们当寿衣也要替你穿上。”
邓明三问:“换了没有?”
三姑娘说:“人家不是一句话没说,衣裳也不接,自己站起来回关他的房子去了。”
邓明三这才舒了口气,骂道:“这些贼攘的,就得八路军治他们。来,老三,给我烧口烟吧!人家那才叫汉子,咱是松三八!抽烟,活一天算一天!”
刘四爷告辞出去,智广也跟着出来,又回到了宋明通处。宋明通听了智广的报告,说道:“这就好了。你还有一个任务,办完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智广问:“什么任务?”
宋明通说:“今天,必须在今天,你想法进宪兵工作队见那人一面,告诉他组织了解他的表现,叫他坚持下去,组织上设法营救他。”
智广说:“这宪兵工作队可不好进,昨天我都到了门口,还给拦住了!”
宋明通说:“你不是认识了两个兵吗?汉奸再硬也怕主子,到他主子那儿想想办法。爷们,想想那个同志的英雄劲,咱有再大困难也比不上他难吧!我知道你准能想出办法来,叫他们知道,老八路厉害,小八路也不熊!”
一顶高帽,把智广戴得心里火热,自己也觉着自己是天下少有的能人了。他拿上存着的另一条烟,直奔洋楼而去。他出门的时候,见刘四爷和宋明通把头凑在一起嘀咕了些什么,然后跨上他的小毛驴,飞跑出村了。
九
上午十点钟,智广到了日军兵营。
因为已是腊月二十九,工地上收工了。日本兵准许民工回家过年,因为他们自己也过旧年。从济南来了个慰问团,有女歌星,有“万才”,还有“文乐”。一些日本兵正在往院内扛衫槁,搭台子。距离兵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陡坡,有个日本军官,骑着辆二六的军用自行车,冲了两次没蹬上去。他下了车,脱下呢大衣,正要往自行车把上搭,一扭头看见智广,就说:“小孩,过来。”
智广走到了他近前。他指指大衣:“你的,你的……”
他下边说不出来。智广就用日语说:“要我帮你拿着吗?”
日本军官吃惊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会说日语?”
智广说:“会一点点。”
“好,你拿着,我冲上去。”
智广把大衣抱了过来,军官蹬上车又往上冲,冲到中途,车停了,还没倒下,智广就从后边推了一把,那军官终于冲上了坡。他从车上跳下来,把车一扔喊道: “万岁,万岁。”他不再管那辆车,从智广手中接过大衣、摸着智广的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一郎”
“中国也有叫一郎的吗?”
“不,这是学校里日文老师给我起的日本名。”
“好,好,你在哪上学?”
“天津,我家在天津,到这儿看亲戚来了,区长是我亲戚。他叫我给皇军朋友送几盒烟来,我送你两盒烟可以吗?”
“当然可以,当然!中国人里也有我的朋友,朋友的烟当然可以收。”
这时一个士兵来向军官敬礼,问他是否需要把车推回去,军官问智广:“你会骑自行车吗?”智广说:“还骑不好。”
“骑上,到我那里玩去!”
智广骑上车,摇摇摆摆。这军官竟然从后边替他扶着,连扶带推一直到吊桥口上。哨兵立正行礼了,他才撒手。哨兵也不再问智广,笑着看他和军官一起进了营房。
这个三角形的城堡,门开在朝西的一面,正对着宪兵工作队那个小围子,相距有一里来地。进了围墙,中间是个三角形的院子,沿着围墙,是一溜红砖白瓦的平房。院子的一头已用土垫起来一个小舞台,四角四个柱子和顶上的横杆,全用红白两色的布缠了起来,迎面横杆上悬着两盏大圆纸灯笼。灯笼上印着日本国徽和“武运长久”的毛笔大字。一些士兵还在最后装饰那个台子。军官领智广到了座北向阳那一排平房中间的一间,帮助推车的士兵赶上去帮他们开了门。
屋子里是日本式的榻榻米,迎面挂了一幅本县地图,地图下边木架上架着战刀。军官脱掉大衣,智广发现他领章上只有四框一线,并没有星,不过是个准尉。
准尉有三十来岁甚至更多一点,矮个儿,胖墩墩,脸上挺死板,只在笑的时候才有生气。他从壁橱里找出一纸盒糖,纸盒口印着一个跑步的运动员,上边有几个日本假名。他问智广:“能念吗?”
智广念道:“苦力果。”
“好,送给你过年。”
“谢谢。”
“你到这儿很久了吗?”
智广说:“有一星期,不,十几天了吧!”
准尉说:“这里老百姓生活很苦。还有,他们对皇军很害怕。警备队,中国的和平军也欺侮他们,是吧?不像天津,是吧?”
“好像是。”
“是啊!没办法,战争!”
准尉说到这儿,点起一支烟,大口大口地吸烟,然后眼睛望着远处吐烟圈。他吐得很圆,烟圈急速滚动着往前跑,一个还没散,一个又追出来。他不再和智广说话了。智广站在一边不知走开好还是再呆下去。
这里立在一边的火炉火小了,这是城市里烧煤块的那种取暖炉。可烧的是木柴,墙根堆了一堆劈好的木柴。智广问他:“我放点木柴进去好吗?”
“好!”准尉像忽然醒过来似的抖一下,问道,“你不是说来给朋友送烟吗?去吧!”
“谢谢了。”智广为他加了一块木柴。
“唔,你的朋友是谁?”
“片山先生和加藤先生。”
“唔,他们住在对面。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加藤先生吗,”智广转了转脑子说,“有一天他到小围子去,走在路上偶然碰到我,听我在唱日本歌曲,就和我认识了。”
“那是好几天以前的事了吧?”准尉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好几天了。”
“是的,那个伤员,好几天没有去看过了,那个人……唔,你去吧,去吧。”
智广到对西屋子找到了片山。
这屋里也是榻榻米,一个铺两副卧具。可有四五个士兵都在屋里说笑,榻榻米上放着一块“栗羊羹”,一瓶啤酒,几个橘子。见智广进去,片山就说:“刚才看见你跟队长一块进来,都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我说是我的小朋友。”
碰到一个会说日语的小孩,士兵们很开心,一个人端起枪冲智广说:“你是不是八路的谍报员?”
智广说:“很可惜,我还没见过八路军是什么样。”
片山推了那人把说:“不要这样,我们只杀和我们作对的中国人。”
那人说:“我是开玩笑,看他害怕不害怕。”
智广说:“害怕就不会到这儿来了!”说着把剩下的烟全从手巾包中倒了出来,几个士兵全笑了,大家伸手去抢。那人赶紧放下枪来抓烟,可他没抢到,气呼呼的说,“不行,把烟放慰问品里,咱们来锤子剪刀布,谁赢了谁先挑,这太不公平了。”
片山说:“不要来锤子剪刀布了,大家平分好不好?”
那人说:“不能给加藤,他给那个八路军看伤,每次宪兵工作队都送他烟,他已经占许多便宜了。”
这几个人争了一顿,仍然把烟平分了。然后又来锤子剪刀布,片山赢了拿了 “羊羹”,他送给智广说:“送你过年。”
这里给队长推车的那个士兵跑来说:“那个孩子还在吗?队长叫他去。”
智广不知出了什么事,心通通乱跳。随那士兵到了队长室,发现邓明三、宋明通两人正恭恭敬敬站在那儿,桌上放着一个大锦盒,两包点心,几瓶罐头,队长脸上仍然死死板板,可也没有怒气。
队长说:“今天放民工回家过年,翻译陪军曹去讲话去了,你替我翻译一下好吗?”
智广说:“遵命。”
队长说:“请他们坐下,唔,你也坐下。我的翻译怎么能在中国官员面前站着呢?”
邓明三、宋明通鞠过躬坐下,说是过年了,皇军辛苦,没什么表示敬意的,送来一点纪念品。他们把锦盒打开,里边是三十几个铁烟盒,盒面上是北京前门的图像。邓明三又指指点心和罐头,说这是送给队长个人的,希望不要嫌寒酸,赏脸收下。
队长板着脸致了谢,又说了几句“中日提携”,“推行第六次治安强化运动”, “要防止八路军谍报人员侵人”等话,就送他们走了。他们刚出门,金队长迎面走了过来。
金队长今天要见皇军队长,把皮袍子脱了,穿了一身“协和服”,戴了顶战斗帽;虽不骑马,却穿一双带刺马针的靴子;虽未挎刀却扎了条挂刀用的皮带。他见准尉在送客,敬完礼后就立正站在一边,准尉当然还要对邓明三说两句客气话,金队长看到是由智广翻译,露出一脸惊诧。恰好准尉送走邓明三后,又对智广说: “我去有点事,你陪金队长进去。”金队长对智广更加估不透了,再三推让,非叫智广先进门,进去后满脸含笑说:“又幸会了。不知道小老弟还会一口日本话,并且和队长相熟。我以前常来,怎么没见你?”
智广说:“我昨天说了,我才来几天,金队长还不放心?”
“不是不是,你跟皇军的关系我怎么不知道?”
“有些关系是不必全知道的,你不放心可以问皇军队长么!”
“明白了,明白了,自己人,自己人。别误会,这么小年纪日语就这么好,看出来不同寻常。”
这时准尉回来了。脸上仍然死死板板的。让金队长坐下后就问:“没什么变化吧?”
金队长叹口气,低下头说:“怪我没能耐,请队长处分。”
“我知道不会有变化的,并不怪你。你勇敢地承担这个任务,精神可嘉。”
“那,按队长命令办吧?”
“明天,过了午夜十二点再办,叫他过个好年!”准尉毫无表情的说,“让他洗个澡,给他一套新的,干净的衣服。要正式出布告,说明他是间谍,不是一般战俘。”
“他不肯换。”
“不用换,他可以把自己的衣服套在外边。我们尊重有骨气的军人。”准尉对智广说,“你可以玩去了。顺便把加藤叫来。”
智广叫来加藤,他装作看人们装饰台子,留心队长室的动静,过了一阵,金队长和加藤都出来了。加藤急匆匆回他自己屋中,金队长凑过来跟智广闲谈:
“你常在队长身边,以后有事还请多关照。欢迎你上我那儿去玩,我们作个忘年之交的朋友吧。”
智广说:“队长很忙,我去打扰合适吗?”
“不要客气,日子长了我要请你帮忙的地方多了。你常跟各个机关各杂牌队伍的人见面,一定知道他们许多内情,这些人有的很坏,敲诈勒索,无法无天;有的暗地通敌,出卖情报,把新政权、新秩序的名声弄坏了,所以老百姓才向着八路军。你再看到有这些不法的事可以告诉我,我来收拾他们。你也算为新政权效力了。我是汪主席领导下的国民党员,我们要靠友邦的协助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和那些土匪不一样。我们是有理想的人!”
加藤扎好腰带,背着红十字皮挎包来了,对智广说:“队长叫你晚上在这看戏。等我回来一块吃饭,你自己在这玩吧?”
智广问:“你上哪儿?”
他说:“我跟金队长去一趟,有点小事。”
智广说:“金队长刚才欢迎我去他那里玩,我不去就失礼了,是吧。不知道金队长是不是只说说客气话,我就当真了。”
金队长说:“不不,你要去我一定欢迎。”说完他却皱起了眉头。
智广说声:“谢谢。”抢过加藤的挎包背上,金队长无可奈何地和他们一块走了。
十
白天小围子院里反比昨夜晚清静,动刑的凳子撤了,绳子解了,邓明三他们打牌的房子
全关着门,连“剿共班”住的宿舍也关着门,听不到一点声音。
加藤问:“怎么这么冷清,他们人呢?”
金队长说:“由那几个犯人领着,起枪去了。”
智广间:“真有枪?这些人…… ”
“有个屁!”全队长说,“有枪的是八路的堡垒户,他们不敢碰!这是些土财主,没有枪!’
智广说:“哟,‘则共班’叫他们骗了?”
金队长说:“他们也知道没有枪,故意打得他们胡说八道,借起枪名义拉回叫他家里人看看,好逼他们拿钱来赎。这帮土匪,皇军的王道乐土全叫他们弄坏了。等他们把钱弄到手我再收拾他们!”
角门口放哨的一见这三人来,立刻从石碾子上跳了下来,举手凑在瓜皮帽上敬了个礼。
加藤等三个人像没看见他径直进了里院。
里院是整整齐齐的四合院,原来这才是地主家的正式宅院。金队长问加藤是否先到队部休息一下,加藤说:“不,先去换药。”金队长就陪他走到南边墙跟,两间堆草的屋子门前。
这里没有哨兵,也没看守,门大开着,屋里有一铺小炕, 一桌一椅,那个穿八路军军装的人闭着眼在炕上躺着,金队长进去,他睁睁眼没动,加藤进去,那人微欠起身来了。智广一露面,那人浑身似乎震颜了一下,但马上又闭上了眼睛。
加藤说:“请先打一盆水来,我洗洗手。”
金队长把头伸出门外喊道:“打水来。”
听到喊声,跑来个人。正是昨晚和智广说闲话的那个。
全队长说:“叫你打水,怎么空手来了?”
“报告队长,我是来请您去讲话的,接太太和老太爷的人马上出发,您有什么嘱咐没有?”
金队长看看表说:“一点了,怎么还不走?”
“等您训话呀!”
“训你妈个X!”金队长冲了出去。那个兵急忙随他走了。
加藤问智广:“金自己去打水了?”
智广说:“不,他去布置人接他的老婆和父亲来过年去了!”
“这个混蛋!”加藤就气哼哼地找了去。
就在这一刹那,那人睁开了眼。这人头发老长,面孔浮肿,胡子拉茬。他一睁眼,智广从那狐疑的眼神中一下认定了他,就急忙小声说:“我代表组织通知你,坚持下去,外边正设
法营救,这两天吃好,他们给衣服就穿上,套在里边准备出去!”
这时外边脚步声近了。那人点点头,又合上眼,嘴角动了一动。
金队长抢先进屋,看看没有异样,随后一个兵端来一盆温水,最后加藤才进来。他洗过手,拆绑带,拆了绑带又洗手,然后给伤者把腿锯断的地方消过毒,上好药,重新包扎起来,
再洗了一次手,从皮包掏出一瓶药来说:“这是止疼的,疼的时候服两片。”
金队长要说什么,加藤拦住他,对智广说:“你来翻!”
金队长说:“这人是日本留学生,他听得懂日语。”
加藤说:“请你不要多嘴,翻,再加上句,日本士兵向他致敬,我尊重有人格的人!”
智广和加藤走出小围子,智广把皮包拿下来还给加藤。加藤问:“队长请你去吃饭,看戏,你不去了?”
智广说:“当然去,可是我要先去告诉我家里人一声,免得他们不放心。”
“对的,早一点来吧!”
“我不一定去吃饭了,戏要看的。”
智广告别加藤, 一路小跑去了乡公所,只见乡公所门口套好了两辆轿车,四个宪兵工作队的兵一辆车上坐了俩,除去两个赶车的外,宋明通也跨辕坐在车上。
智广奇怪地问:“乡长,你也进城?”
宋明通说:“你快来说说情吧,这几位老总非拉我一块去。这大过年的我走得开吗?”
和智广谈过天的那人把头从轿门伸出来说:“翻译官,你别管闲事。这是金队长的命令,叫乡长陪着去,出了事先枪毙他!”
智广心想我多咱又成了翻译官呢?也不去争论了,只对宋明通说:“那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凡你嘱咐办的,我全能办。”
宋明通说:“也没啥。你家带话来了,今天下午再玩一下午,天亮前赶回家包饺子去吧。就别太贪玩了。”
车把式问过宋明通是不是出发,宋明通点点头, 一阵哈呼,车就朝村外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