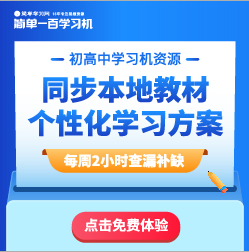十一
既然现在不走,智广决定去洋楼再了解点情况。他到洋楼时,演出已经开始了。日本兵都盘腿坐在地上横放着的木料上,除去日军,准尉还请了各据点伪军伪机关的关目。金队长,
八字胡,麻子脸都在座,邓明三也来了。
这是日本一个什么“后援会”和山东新民会联合派来的慰问团,除去演节目,还带来一堆“慰问袋”。慰问袋白布缝成。上面印了日本国旅,写着歌颂战争的俳句,还有日本女人、
孩子和风景的漫画,里边装了糖果、刮脸刀、小镜子、针线板之类小物件。准尉下令给汉奸头头们一人也发了一个。日本兵当场都打开把吃食拿出来吃了。几个中国人全双手捧着它像
圣物一样动也不动。
智广在场外酸巡了半圈,准尉看见了他,朝他招手。他本想不过去,看见坐在一边的金队长正拿眼盯着他,他就大大方方走到准尉面前,行了个礼。准尉说:“坐在我旁边吧。”智广说:“谢谢。”就坐了下去。准尉对坐在后边的邓明三说:“你这个孩子很好,我很喜欢他。”
这时一个没见过的日本二等兵,讨好地把话翻译了过去,邓明三连连点头致谢,说:“孩子小,不懂事,请太君多指导。”那个兵又把话翻成了日文,而且加了好多谄媚词。智广听他不论说中国话还是日本话,都带点怪口音,就知道他是那个高丽翻译。这个人跟汉奸头目们勾结,敲诈勒索,杀人害命和卖毒品无恶不作,不少人到敌工部报告过他的罪恶,智广不由得就多看了他两眼。这人从服装到姿势全模仿日本士兵,模仿得不算不像,可脸上一股狡诈气、馅媚气却是日本兵脸上少见的。日本兵有的残忍,有的蛮横,更多的狂做,却没有这股奴才相。
这倒是汉奸们脸上常带着的。
高丽翻译发现智广看他,就点点头。演出开始前慰问团长请准尉上去讲话。高丽翻译跟着站了起来,准尉板着脸说:“我不准备对中国人讲话,用不着你。”
队长刚离开,高丽翻译就活跃起来,先是打开慰问袋吃食品,故意嚼出声音,用日本话说:“啊,真好吃,真好吃。”一边用中国话对那些汉奸头头们说,“你们打开尝尝嘛,好吃极了。我们日本点心不像你们中国的油腻腻的,好吃极了。”他见智广不理他,又主动凑过去说,“我叫金井一郎,翻译。”智广说:“你的中国话我听不大懂,还是用你自己国家的语言说话吧。”翻译先是瞪了一眼,马上又笑起来,改用日语说了一遍,并且补充说:“您是外地来的,我的中国话为了叫当地人听懂故意用山东口音了。”智广装作不知情地用日语问:“你好像不是东京人。”金井说:“噢,你会说日语,太好了,我是釜山人…… ”
这时不知准尉讲了什么,全场都高呼起“万岁,万岁”。汉奸们莫名其妙,赶紧也跟着喊。
准尉讲完话下来,节目就开始了。
邓明三把头凑近智广问:“他们看戏兴拍巴掌吧?”
智广说:“兴!”
邓明三说:“啥时候该拍巴掌,你捅我一下,别让我误了。”
这是一套杂八凑的节目。有日本相声,有文乐,还有中国人用口琴伴奏唱《四郎探母》。准尉正襟危坐,不断地吸烟。汉奸们两眼发直,只有在演日本相声时士兵们哈哈大笑,金井也笑,故意笑得声音比别人大。准尉白了他一眼。他把头低下去了。智广往后边瞧了几次,没看到加藤,就问准尉:“加藤君坐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看看他去吗?”
准尉说:“他刚刚出诊回来时还好好的,忽然犯了胃病,疼得厉害,向班长请了假。你可以看看他去。”
加藤住在西侧,智广故意从东侧出来,这样他就绕着院子看了一圈。原来他没到过的南侧是伙房和仓库和炊事兵的宿含。每个炮楼下层都是勤务室,装有电话。挂着士兵们的名牌。
他找到加藤的房间,敲了下门,里边沉闷地应了一声。他进去看见加藤靠墙坐着,在闷闷地吸烟。
“噢,是你,早来了吗?”
“看了一会演出,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怎么不休息?”
“好了一点,谢谢你。演出有趣吗?”
“我不觉得很有趣。”
“这算什么戏班子,把这种下等玩意给当兵的看。”加藤摇摇头说,“我不想看他们。”
过了一会,加藤问道:“你过了年就回天津吗?”
智广说:“我想是。爸爸没有来,妈妈不放心。”
“走吧。”加藤望着窗外说,“我是老师,我有责任教育学生要善良、正直,在这儿你找 不到摹仿的榜样。”
“嗯?”智广正色地问。
“唔,我是说这据点里你见不到高尚的人,小孩子不适宜在这种地方生活。”
“我明白了。”智广试探着说,“你认为,今天你去给他换药的那个人也是下流的吗?”
加藤吃了一惊,看着智广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久,结结巴巴地说:“你年龄还小,有许多 事不是你这年龄的人应当知道的。”
智广说:“我知道加藤是个好心人,好老师,和许多人不一样。”
“你凭什么说我是好心人?”
“你给那个人换药很认真,而且尊重他!”
“唉,千万不要说出去,你答应我不跟任何人说!是吗?”
“当然。”
“那个人是我们的敌人,在战场上见到也许我会杀死他,或者我被他杀死。可他,他是 个品格高尚的中国人;外边看戏的那些中国人是猪,是狗!……”加藤突然住了嘴,被自己 吓住了。
智广催促说:
“您往下说呀!”
“没什么,没什么,我今天病了,乱说了一气。”加藤摇摇头,不再说话了。
外边人声嘈杂,演出完了。智广站起来告辞,加藤说:“队长要请来看戏的中国人吃饭,你不留下吗?”
智广说:“如果我能和你两个一起吃我就留下。”
加藤说:“不行,我是士兵,最低一级的士兵,没这个权利留你。将来吧,将来退伍以后可以一起吃饭。”
又有人敲门了。金井探进个头来说:“学生,队长先生请你去吃饭。”
智广只好随他走出来。
尽管是冬天,宴会就在院中进行。士兵们把看戏坐的木料拉开,围成个方形,用子弹箱架起木板作为长桌,然后每人一份摆上了碗筷和酒杯,搬来了几木桶清酒。日本士兵按建制坐好,准尉就让中国人就座,炊事兵先给每人送上一小盘鱼片和酱油碟,随后又送来“天妇罗”。准尉举着杯说了些祝贺新年,希望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等话,就推说“还有公事要办,不能陪大家,希望各位尽兴”,回自己屋去了。
汉奸们夹块生鱼放在嘴里,嚼嚼不是滋味,想吐出来又不敢吐,有的人就大口喝酒,像送药似的往下送。有的装作擦嘴,把它吐到袖口里,扔到地上怕日本兵看见,只好用手攥着。
过了一会,金井又来传话,队长请区长和智广去他屋里谈话。
原来准尉在屋里自己单独摆了一份饭,这时他已吃完,叫勤务撤下食盘,端上茶来。让他们坐下后,准尉就问邓明三,智广家里有什么人,父亲干什么。
邓明三当过土匪做过生意,说谎可满有经验,就说他弟弟原在大连满铁做工,后来调到天津, 一直在铁路上干活:除去智广外,他弟弟还有一儿一女,全在天津;智广放假回来过
年,过完就回天津去。
准尉说:“你弟弟靠做工,供三个孩子上学不容易吧。”
邓明三说:“所以我常补贴他们。”
准尉就说:“我很喜欢这个孩子。如果他父母跟他自己愿意,我想收养他。在我的部队里有人当过教员,可以教他知识,他随着皇军部队还可以使思想纯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
样的人才有前途,你看怎么样?”
邓明三眨了半天眼说:“谢谢队长好意栽培,不过我得跟他父母商量一下。”
准尉问智广:“你愿意跟着我吗?”
智广说:“我要回去问妈妈,我一切听她安排。”
“好的,好的。皇军也尊重孝道。不孝哪里有忠?你们去吧,早一点商量好告诉我。”
十二
原来听说金队长太太要来,邓明三吩咐备车的同时就叫人赶紧扯布买棉花,找人做了两床新被窝,晚上进小围子时带了进去。走到角门口,就请哨兵报告金队长,说区长送礼来了。
官不打送礼的。这礼物不重,可送的是地方。金队长亲自迎出门来,笑着说:“这怎么敢当?”破例把邓明三请到“宪兵工作队”院里去吃茶。
“宪兵工作队”院里正在杀猪,宰鸡,靠西边一溜兵营的檐下挂了一串日本纸灯。智广看了一下,被俘干部那屋的灯也亮着,全队长一直把他们让进堂屋。
堂屋是一明两暗的房子,外间屋靠墙放着个八仙桌,桌旁有个五十开外穿长袍的人正在一叠白纸上写布告之类的东西。对面墙上一张条几,条几上整整齐齐平放着许多书和本子。
智广看了一眼,发现全是根据地出的小册子和敌伪编印的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的资料——“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二五减租”,《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向何处去》等等。他想仔
细看看,金队长过来客气地把他让到东间屋去了。
东间屋是金队长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全队的名牌,本县地图,地图上把八路军的根据地、游击区全用红笔勾了起来。窗下一个洋式办公桌,桌上放着一本《曾国藩家书》,一本言情小
说《北雁南飞》。旁边一个桌上还堆了些旧书和日文书。
金队长请他坐下之后,勤务兵送上茶来。
邓明三笑着说:“一看队长这办公室,就知道是个有学问的人。不像我们这些粗人。”
金队长说:“哪里,还是区长经验多,民情熟,从政有方。”
邓明三问:“你看这么多书,想学点啥呢?”
金队长说:“就是要找个治国之道。圣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不治天下何以能平?咱们中国又穷又弱,四万万人如一盘散沙,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是注定要当亡国奴的。
‘中央派’得了势,中国亡于英美:共产党得权,中国亡于赤俄。所以汪兆铭主席毅然决然投向和平阵营,重建国民党,寻求救国之道。日本虽然也要取我们的利益,可他到底还是亚洲人,同文同种,尊孔信佛。只要我们与他共存共荣,打倒英美,建立东亚新秩序,他们并不想灭我民族,还是能保住我们的国号的。现在不是挂青天白日旗了吗?当然,要尊重人家为盟主。那有什么办法,谁让中国弱呢!弱肉强食,天意如此!所以我最恨八路军。抗日抗日,这日本是你几个土八路抗得了的吗?要没他们,皇军就不会扫荡。不扫荡,天下不就太
平了?老百姓少受多少苦!”
智广听得又气又恨,极力压住自己想批驳他的冲动。邓明三却打起哈欠来了。金队长忙说:“你看,我又犯了书呆子的毛病了,大过年的谈什么政治呢?来,看看我的卧室去。”
他领两人到了西边那间屋。
原来全队长去皇军部队看戏的时间,他的部下已把这间房收拾好了。红暖帐,红椅垫,都是“剿共班”扫荡时抢来戏班子的东西送给他们的,新毛巾新肥皂是他的部下凑钱买来孝敬的。邓明三说:“现在车也快到车站了!”
金队长说:“刚才宋乡长从县里摇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了县城啦。明天头晌午准能赶到,决不耽误三十晚上送神!”
“那更该道喜了。”
“我请客,我请客,过了年我这儿就清静了,欢迎你们常来玩。我跟你们学学平胡断么门前清!”
“怎么,队长不会打牌?”
“我会打派司,可这儿找不着手,麻将也会,可打不好。”
胡说了几句,邓明三就告辞出来。
“剿共班”今天图古利,也不过堂了。昨天起了一天枪,屁也没找到。可主人家一看当家的打得皮开肉绽,没了人形,当场交出地契顶枪款,由他们卖地,也算发了利市。这晚上全班放假,公开招赌,各个屋推牌九的,掷骰子的,打麻将的全都热闹起来。邓明三他们也玩了个通宵。“剿共”班长赢了钱,吩咐厨子伺候一顿夜宵不收钱。
智广心里惦着营救过路干部的事,坐立不安,早早自己上炕躺下,折腾半宿还没睡着。后半夜才睡过去,第二天醒来已是半晌午了。
“剿共”班长又请了赌客们一顿早饭,肉丝面条大馍馍。饭吃完,邓明三说金太太也快到了,不如到金队长那儿贺个喜,接到太太再散。其余几个人也都受宪兵工作队的辖制, 一听这消息,就埋怨邓明三有进身的路子自己捂着,不让别人沾边,很不够朋友;马上派人去买水果、洋糖给金队长太太接风。这消息报进去,金队长更是高兴,便叫人把大伙全请了进
去。
进到堂屋,人们看见桌上一叠布告,地上竖着个牌子,就吃一惊。再一细看,牌子上写着:“抗日犯无名氏一名”,名字上还没勾红。八字胡就问:“怎么,年三十了队长真要出红差?”
金队长说:“不到这地步,我也不敢请你们进来。这几个月多有得罪,皇军的命令,概不由己!”
“什么时候出斩?”
“皇军说言而有信,等他到底。三十晚上十二点再问一回,不降就斩,决不拖延了。”
智广远远往过路干部住的房子一看,果然上了锁,心中便像热油浇的一样难过:到半夜还有十几个钟头,天兵天将怕也来不及救他出去了。
金队长摆上烟茶糖果,陪大家说了一会闲话,看看十点多了,人还没到,就有点急。问道:“早上五点火车,现在该到了,怎么还不来?”众人说:“太太尊贵,车不敢赶得太急,多走一会是必然的。”又瞎聊了一阵,金队长看看表十一点半了,就更沉不住气,喊下边集合一班弟兄,上公路上去迎。人刚集合好,哨兵跑来说:“队长,接太太的人回来了。’
金队长问:“车呢,停在吊桥外边了?”
哨兵说:“这我还没看得。”
“混帐,还不看看去。”
正说着,去接太太的四个兵有一个进来了。队长便问:“车到了吗?”
那人变颜变色地说:“还没有。”
“还多远?”
“二十里地。”
“什么,你们怎么闹的?”
“车坏了,太太又不能走路,没办法。只好停下来修车。”
“太太跟老太爷就这么冷的天坐在路上等着?”
“没有,那旁边不是鸡鸣寺据点吗?我们说了一下,据点的警备队长说认识您,他把老太爷和太太接进据点去歇着了。老太爷怕您不放心,写了封信叫我先送来,说不用急,下午准到,误不了送神。”
金队长脸上这才有点温和气,骂道:“你们这群笨蛋!白拿粮食养活你们了!这点事也办不好,等太太到了我再跟你们算帐!”
金队长接过信,打开来仔细看。送信的兵目不转睛盯着他的脸。全队长眼睛一瞪,当兵的就打了个哆嗦。可金队长捭了会眼又笑了,当兵的这才舒了口气。
“各位,家父和残内要下午才到,我就不敢再留你们了,都挺忙,还是自便吧。”
众人都是会看眉眼高低的,见金队长心里不痛快,就借机告辞。邓明三也要走。金队长说:“您留步,我还有事请教。”
邓明三满心狐疑地站住了。智广也停了脚步。可金队长说:“我跟区长有点小事要合计。
小世兄,你听着也没意思,你玩你的去吧!”
智广只得满心狐疑地走出了小围子。
这时距吃饭尚早,刘四爷、宋明通又都走了,智广无处可去,便在村里闲遛达。
小土围子在街北头,挨着围子附近,有个小院,门口贴着“马蜂坞戒烟局”和“宣抚班”的牌子,对面就是警察所。警察所已上门了,门口有辆小平车,摆着烟卷、洋糖和当地少见的苹果。苹果摊旁边有个卖烧鸡的,有几个伪军倒背大枪在抽干子。再往北走,两边店铺都上了门,冷冷清清就不见人影了。从大街上顺个巷子走进去,拐个弯就是个场院,隔着场院有几户人家,有的在当院竖灯竿,有的在院外推碾子。尽管在敌人鼻子底下生活,仍在按习惯办年。智广走过去看看,人家见他是从据点过来的,便不理他。他见墙根底铺了张席子,晾了一席鸡毛,就搭讪着问推碾的人:“晾这些鸡毛干啥用?”
推碾子的是个老婆婆,就顺着说:“拿硷煮了,晾干了做褥子。”智广问:“谁家杀这些鸡?”
老婆婆说:“还不是你们据点里,老百姓谁杀得起?”智广问:“这鸡毛是你捡来的?”
老婆婆说:“我进得去据点呀?是那个高丽翻译官抱来的,叫我给他煮,给他做。煮得锅恶臭,大过年的连馍馍也没法蒸,天下哪里找这些鳖孙去?”
智广问:“为什么他单来找你?他怎么认识你家?”
老婆婆说:“日他娘。夏天俺儿媳妇去拔麦子,回家晚了,从洋楼东里经过,洋楼里鬼子嗷嗷叫了两声,谁懂他叫的啥呀?俺媳妇吓得就匍匐下了。谁知道这一来犯了忌,当,当,洋楼鬼子就是两枪,正打在俺媳妇胳膊上!有看见的送了信来,俺全家哭着喊着去找宋乡长。
宋乡长进洋楼说了情,才领俺去把孩子抬回来。谁知道第二天来了个背皮包的鬼子跟这个高丽翻译,鬼子说昨天洋楼上问是谁,俺媳妇没回答,他们开枪打错了,对不起俺了,要给媳妇看伤。俺不叫他看,他非看,日他娘,又惹下麻烦了。”
智广问:“看伤又惹啥麻烦?下毒药了?”
“药倒是好药。可看完伤,他前脚回去那个高丽翻译后脚又回来,说是皇军来看伤不收药费,你家总得给个鞋钱,买盒烟卷吧?看一回要一回,那鬼子装好人看伤,暗地派高丽棒子来要这要那。这高丽人还说,钱是给皇军医官的,他分文不要,只求俺给他干点活。今天洗衣裳,明天拆被窝,日他娘,打了俺的人还讹上俺了,过年又叫俺给他煮鸡毛!你年轻轻不学好,跟他们混什么劲?”
智广并不解释,讪笑着走开。心想金高丽打着加藤的旗号敲诈勒索,加藤还被蒙在鼓里。有机会应当告诉加藤,治那小子一下。
智广又往前走,找着条胡同,又拐回大街上,恰好从对面胡同出来一个骑驴的女人,后边跟着个半大小子。那女人穿一件黑土布薄棉袄,蓝土布棉裤,头上罩了黑帕子。已经擦身走过了,那女人忽然拉住了驴,叫道:“小先生。”
智广听着口音耳熟,走近一看,原来是三姑娘。三姑娘换了衣裳,也没施脂粉,又少了背后的大辫子, 一下老了有十岁,像个四十多岁的乡下大嫂。智广问道:“你,你这是上哪儿去 ? ”
三姑娘说:“我也回城里家去过年。我家有个病爹,瘫在炕上。不去看看,我心里不妥帖。”
智广笑笑说:“你这么一打扮,我不敢认你了。”
三姑娘说:“这个样是我的本相,那个样倒是打扮出来的。衣裳,辫子,耳钳子全是借帐置办的,不作营生舍得穿呀?还指着它挣钱呢!”
智广说:“你的心挺好,干那个下贱事干啥?换个营生吧。”
三姑娘眼圈一红,叹口气说:“俺爹有病,欠了人家钱,把我当出去还帐的,再有两年把帐还上,我就不干了。要有人收我从良,天边我也去,咋伺候我也情愿。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谁愿意自作下贱呢。”
说着,三姑娘从她挎着的小包袱里、掏了半天掏出一挂脆枣,递给智广说:“过年了,我没啥送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都是办大事的人,老天保佑你们!”
智广说:“这我可不敢要。”
三姑娘脸刷的一下红了,眼睛转了转泪花:“嫌我这东西来的不干净吧?”
智广忙说:“不是!”
三姑娘说:“再不济,我的钱也比那些人的干净!”
智广笑着说:“我要,我要。我是觉得你帮了我不少忙,我没啥给你的,不好意思。”
“你看得起我,拿我当人,比送啥都强!”
智广接过脆枣,冲她点了一下头说:“多谢你了。”
三姑娘抖抖缰绳,小毛驴得得地往南走了。智广一直看她走远,心想:“这跟我在集上看见的真是一个人吗?”
智广提着这串脆枣,走到乡公所。院子里没有人,显然都回家过年了。正在踌躇,忽听有人压着嗓子喊他:“小邓。”
“谁?”智广看看,周围没有人。
“进来,我在屋里。”
智广听出声音来自西屋,就推门进去。 一看吓了一跳,跟他同属于一个交通站的老魏在炕沿上蹲着呢。
老魏说:“你上哪儿去了,我等你半天没回来?”
智广说:“你来干啥?”
老魏说:“上边叫你马上回去, 一分钟不要在这儿停了。”
智广说:“我还要听听那个干部的消息。”
“那不是你的任务,你的任务完成了。快走,执行命令。”
智广无可奈何,饭也没吃就上了路。幸亏三姑娘送了那串脆枣,他全吃进去,找个人家要了碗米汤喝,才走下这十八里路来。快到目的地前,远远看见公路上两辆轿车,车辕上跨着的像是宋明通,后边还有三个扛枪的护卫着,急急忙忙奔马蜂坞据点赶去。
十三
智广回去并没有紧急任务,汇报完之后跟同志们一块烧了锅水洗洗澡,换下学生装,穿上公家发的棉衣过了个热闹年。他一直想打听过路干部的事,可站上没有人知道。领导当然知道,谁敢去问呢?想等老魏来问个究竟,老魏一直没回来。
过了正月十五,老魏才回来。智广忙去找他打听。
“那个被俘的同志到底怎样了?”
老魏说:“还怎么样?叫敌人枪毙了!”
“我不信,你别蒙我!”
“不信你去看哪,我揭回一张敌人的布告来,在领导屋里哩!”
智广装作有事报告,去找领导,果然在桌上看到张布告,就是在金队长屋里看见过的那一种,连字体他都认得。他心里立刻揪得发疼,问领导说:“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马蜂坞街上贴满了!”
“那我不是自去了?没有完成任务。”
“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该看的看了,该说的说了,别的就不是我们所能负责的了!”
智广好几天舒不开心,并且觉得他的领导太狠,对同志连点痛惜的感情也没有。
刘四爷照样骑着驴四处赶集,开春后敌人又来了次扫荡,但规模很小,并且被我们打了个伏击打退了。扫荡的第二天,刘四爷赶马蜂坞集去收税,带回一个消息:从来不参加扫荡的“宪兵工作队”这次主动要求参加了扫荡,在金队长和“剿共”班长并肩撤退时,“剿共”班长中了我方枪弹当场阵亡了。
半个月以后,刘四爷又带了个消息,“剿共班”的人告了金队长一状,说“剿共”班长不是八路军打死的,是中了金队长的黑枪。因为金队长找“剿共”班长要走一具撕了的肉票,冒充八路战俘,打了一枪埋上了,真八路干部却放走了。日军队长把金队长抓去审了一阵,用刺刀挑了,还派加藤去挖出尸体检验。验的结果是真是假,却无人知晓。
数月后邓明三的任期已满,日本人解除了他的职务。不少人都花钱运动要继任他的区长。
宋明通出的价儿最大,“皇军”把区长的官衔给了宋明通。宋明通从前院乡公所搬后院区公所去了。
十四
宋明通的伪区长干了半年多,战争形势起了根本变化,日本要收缩战线,撤销了马蜂坞据点。撤退时伪军在前,伪机关居中,日本兵殿后。宋明通没机会脱离他们,便随着进了县城。
我们的力量增强了,部队就进行大整编,邓智广的单位全建制南下,并入了新四军的序列。日伪据点拔掉之后,农村里就开始了“除奸反霸”运动。宋明通心想,领导人和联系人全南下了,找不到人为自己证明,回到村里若被人当作真汉奸除了怎么办?便在城里住了下来,靠做小买卖为生。他去天津办货,赶上我军破坏津浦路,又把他阻在天津回不来了,从此就彻底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天津当了店员。解放后他背着重大历史问题在一个小杂货店卖酱油,多次找证明人都没找到。“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就被“深挖”出来,定成历史反革命,关进监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院清理旧案,又派人查证,意外地找到了邓智广,又从邓智广那儿打听到他们当年的领导。真相大白,宋明通这才重见天日。这时他已是七十来岁的老人了。出来之后他办了两件事, 一是申请重新入党, 一是写材料为邓明三争取从宽处理。随后就退休了。
邓智广去年回家乡探亲,见到了他。他正在研究园艺技术,买了不少书,读得挺认真。
但从他菜园看,效果不大,还没有不读书的人家那菜长得好。看来到老还是“二八月庄稼人”!
一个意外的消息是,他儿子怕受他牵连,始终没敢回老家。国民党占据济南、青岛时,他在美国军舰上找了厨房的工作,随船去了美国。宋明通拿给智广看他寄来的照片, 一家人站在他开的中国餐馆门前,老婆也是华裔,两个孙子长得很像宋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