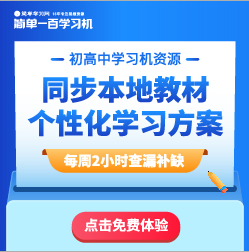会议的促成和召开
长征开始以后,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首先在领导层中,对于当时的军事指挥错误就有议论,早已酝酿着不满。记得早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张闻天同志就曾对我说,李德这样指挥怎么行?这样能打胜仗吗?有一次军委开会时,张闻天同志严肃地批评了同敌人死拼的错误方针,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结果引起了博古的不满,指责他的态度同普列汉诺夫对一九○五年俄国革命一样。张闻天当然不服,两人就争执起来。李德忙出来当"和事佬",说这里的事情还是要他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办,他们不能自相磨擦。张闻天却不理这一套,对博古说,中国的事情不能全听李德的,应该自己有主张。由此可见,他后来能支持毛主席并不是偶然的。但是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他当时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因为负过较重的伤,身体很不好,在长征的行军途中,只得每天坐担架,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在行军休息和宿营时,经常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问题。经过不断交谈,王稼祥同志赞成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随后他又同张闻天等同志交换了意见,大家都支持毛主席的主张。张闻天同志早对李德有意见,周恩来、朱德同志本来就很尊重毛主席,当然也是支持的。加之党内军内普遍感觉到中央的军事路线有问题,所以在长征行军途中,已为后来的遵义会议作了思想准备,所以毛主席得到大家的支持并不是偶然的。王稼祥同志第一个促成了会议的召开,张闻天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胜利攻占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中央决定,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公馆的小楼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陈云和朱德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分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他的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会未开完就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没有及时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
会议过程中,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日常事务,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会议前后共开了三次。开会的具体日期是在一月十三日到十五日。一月十五日有份电报说,彭德怀同志已回前方,会议仍在进行。保存下来的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上印的日期是一月八日,我看很可能是一月十八日之误。因为一月八日部队刚进遵义,中央领导机关一月九日才进城。还没有来得及开会议,决议不会那么早就作出来。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一张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不象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会议的内容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重点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揭露了军事教条主义的危害。会议的主报告是博古作的,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作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一向谦虚,在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态度。
毛主席稍后作了重要发言。通常他总是先听听人家的意见怎么样,等他一发言就几乎是带结论性的了。这次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主席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和朱德同志也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也表示完全同意毛泽同志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他又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积极支持。别人的发言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严厉,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他曾写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军事路线。会议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确是王明路线的一员干将。他在会上实际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他基本上是一言不发。聂荣臻同志长期与他共事,对他早就有所认识,那时就看出了他的毛病。别的同志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会上重点批判的是博古,同时批判了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完全是个处在被告席上的受审者。我坐在他旁边,别人发言时,我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他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次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议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短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东西。事后有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还把烤火盆也踢翻了,把桌子推翻了,这我没见到。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会议的结果
这次会结束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领导,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时,又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撤离遵义以后的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次会议对于"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已经作出了结论,改组中央领导的决议,也已向部队传达。倒有一个人,最后还坚持错误的立场,力图为"左"倾错误辩护,他就是凯丰同志。他在会上态度就不够好,会后我又曾听他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博古同志虽然有错误,但他的态度还是照顾大局的。他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中央的挑子(当时中央是有几担装有文件和党中央印章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
在遵义会议上,李德被撤销了中央的军事顾问职权,一月十九日撤出遵义,我还同他在一起。他自己提出要求跟一军团行动,中央同意后我随他到了一军团,过了桐梓,又继续前进。这时林彪同李德虽然不再多接触了,但李德要求到一军团来,显然还是对林彪感兴趣的。林彪交代军团管理科一个大个子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每到宿营地,那个科长总是亲自为李德号房子,在最适中最安全的地点挑比较好的房子给他住。部队打土豪得来的东西,也给他提供最好的一份。但是他的情绪已经很不好了。第二次进遵义时,有一回我去他屋里,见他桌上摆了一堆核桃,还有把小锤子,看来他自己刚刚敲了吃的,我也就随便敲了一个吃起来。谁知道他正肚子里有气无处发泄,突然拿我出气道:"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跟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真叫人哭笑不得。后来我被调到三军团工作,有一回司令部得到一些炼乳、咖啡和香烟等,杨尚昆同志叫我送些给李德,我真的送了些给他,他一见又说我真是个好人,没有忘了他。他自己当初动辄骂人训人,好象倒都忘了。
会议的后话
在以后的长征途中,我还遇见李德几次。过草地张国焘搞分裂后,有一回,原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同毛泽东等同志争吵,他要拉人随张国焘南下,我和李德也在场。据说李德当时也是反对南下的,不过我看他未必是出于拥护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而是希望尽快北上,好靠近苏联,重新接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李德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到陕北,在那里帮助训练过骑兵。一九三六年十月,斯诺到保安访问过他,他对于遵义会议对他的批判和撤销他军事顾问职权,仍然是不满的,有一肚子牢骚。当时中央分配李德到红军大学讲战役学,周恩来同志指定我再去为他当翻译,我很不乐意地对周恩来同志说:"让我干什么都行,再也不愿当李德的翻译了。"周恩来同志苦口婆心地对我作说服工作,最后我还遵从了他的意见。于是,我同李德又共了一段事,对我们过去的不愉快关系,也就不计较了。
一九三九年夏,我党送李德自延安经兰州返回苏联。正好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任处长,负责接送并具体安排他回苏联。他乘周恩来同志到苏联治病的飞机同机到达兰州。将他接到办事处后,我立即同苏联驻兰州的代表机构联系,将李德的情况向苏联同志作了介绍,请他们负责下一步安排,送李德回苏联去。苏联代表也已得到通知,接手安排他回国。我在兰州同他作了最后的告别。他一九三二年来到我国,当时才三十多岁,在我国活动六年多,其中同我共事就近两年,我亲眼看到了他最神气和最失意时的样子。现在要同他正式分手了,本应该相互作些表示,但是他的情绪十分消沉。他大概想到自己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到中国工作几年,却没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回去无法交代,心情的确是沉重的。临别时,我带点讽刺地对他说:"祝你回苏联以后,能走好运,一切顺利。"他听了只是苦笑一下而已。据说他回苏联以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批评了他,从此不再"官运亨通"了,被派到苏联的外文出版社搞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被送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度担任过东德的文化工作方面的职务,还曾出版过一本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回忆录,书名叫《中国纪事》。书中内容完全是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的,继续坚持并宣扬"左"倾教条主义,反对我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竭力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可见他至死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我们来说,这倒是一本难得的反面教材。应该指出的是,他在一九六四年以后直到一九七三年写成此书,完全是为着反华大合唱的需要。为此,我曾撰文对李德此书进行了批驳,发表在《红旗》一九八一年二十一期上。
我在为李德作翻译期间,由于工作关系,同王稼祥、张闻天和博古同志也有过较多的接触。我同他们认识较早,一九二五年曾同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同船去苏联,并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博古还比我们晚一年到中山大学。我对他们还是比较熟悉的。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在中山大学时,就是活跃分子。他们的英文底子都很好,张闻天同志还曾留学到过美国,王稼祥同志是教会中学毕业的,也上过大学。到中山大学后他们又特别用功,体育活动、文娱活动都很少参加。这一点我同他们不一样,我从小就喜欢体育活动,所以大凡有同校外的比赛,我都要参加。这就不如他们读的书多了,所以他们很快掌握了俄文,成为翻译,后来还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
博古是一九二六年底到中山大学的,他这人活跃得很,他一来,就到处听到他的声音。他也有些英文底子,掌握俄文也比较快,他同张闻天、王稼祥同志比起来,不象他们那样较稳健,有学者风度,而是锋芒毕露,处处表现出政治活动家的味道。他在中山大学时就是这样,后来当了中央负责人,直到遵义会议以前,他都是这个样子。
尽管博古等同志在中山大学时曾参与了王明的教条宗派,回国后又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但是他们都较快地认识和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服从了党的决议,为人是正派的。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个人的品德也是应该肯定的。毛主席多次说过:王稼祥同志是第一个从教条宗派中脱离出来的。他在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方面是有功的。张闻天同志也曾起了重要的作用。毛主席说,如果没有洛甫(即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博古同志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也是端正的。延安办的《解放日报》,博古任总编辑,他写的社论、文章,很好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这些同志在遵义会议以后,在民主革命中,在新中国创建以后,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他们的贡献,所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仍然应该有他们的适当位置。
【伍修权(1908—1997),湖北武汉人。早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及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后在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回国后,曾任闽粤赣军区分区司令员、第三军区副参谋长、第三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长征途中列席参加遵义会议;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处长,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作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沈阳小组中共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沈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及沈阳卫戍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苏联东欧司司长。195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衔特派代表率领新中国首个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是中共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