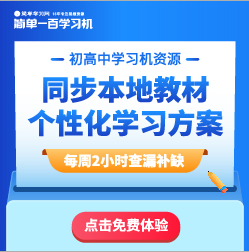三、深夜赎票
张秀庭到“朱记石灰行”时,那里尚未开门营业。但因这是一处前店后宅格局的所在,所以前面的大门已经开了。两个学徒正在扫地,见到张秀庭,他们的神色似乎有些异样。一开始张秀庭还没有在意,他进去后,穿过第一进店堂,进入第二进,那是库房和账房以及学徒和住店伙计的寝室。再往里的第三进就是朱老板的内宅了,此时还早,他不便擅入,于是就进了账房。
账房里,刘先生正坐在账台上“呼噜噜”地吸着水烟。见张秀庭忽然出现,愣了一愣,马上放下水烟筒迎了上来,待要呼叫学徒张罗招待,已被张秀庭打个手势阻止了。双方目光接触时,张秀庭明显地感觉到刘先生那双眼睛似乎在故意回避着他,不肯或者不敢跟他的目光正面接触。这就令张秀庭不解了,记得昨天来勘查询问时,这位刘先生是很积极热情的,不管是回答问题还是招呼其他人来接受刑警的调查,都是目光灼灼,无所顾忌。仅仅隔了半个晚上,他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张秀庭这时回想起刚才进店时所见到的那两个学徒的情景,跟刘先生这副神态联系起来,就觉得有点儿怪怪的了。但他此刻不便开口询问什么,于是就坐了下来,问刘先生:“朱老板昨晚睡得晚,又肯定没有睡好,不知道这会儿起来了吗?”
刘先生回答前眸子里闪过一丝为难的眼神儿,顿了一顿才轻声道:“哦,我还没去过后面,不知朱先生这会儿起来了没有……嗯,张同志是个大忙人,屈尊前来公干,不能让您久等的,我这就去看看,请朱先生赶快过来。”
刘先生说着起身出门去了后面。张秀庭坐在那里,随手从账台上拿起一份报纸,刚要看时,从楼上传来一个男童的声音:“我要吃热干面!”
这就是令张秀庭眼睛发直的原因了:朱家这边只有一个男童,这不是昨天报案称已经被“立早鱼”绑架去了的朱清霖吗?怎么回来了?回来了报案人朱维鑫又为什么不对警方说呢?
张秀庭自然不想看报纸了,站了起来,走到账房门口。这时,正好女佣夏妈从账房门口的中间通道出来往前面去叫学徒吃早饭,张秀庭便问:“你家小少爷要吃热干面?”
夏妈神色大变,不敢正视张秀庭,眼珠子转了几转,双目视地,嘴里支支吾吾不知吐出了半句什么话,然后连连摇头,慌慌张张走了。张秀庭望着女佣的背影正寻思这是怎么回事儿时,刘先生从内宅出来了,冲他拱手:“对不起!让张同志久等了。朱先生已经起来了,马上出来!”
张秀庭退回原位重新坐下,干脆直接问刘先生:“小少爷在家?”
刘先生此刻已经恢复了昨天的正常神情,目光也敢与张秀庭对视了,只是声音有点儿轻,像是底气不足的样子:“这事……嗬嗬……一会儿朱先生会向张同志当面奉告的。”
说话间,朱维鑫进了账房,冲张秀庭连连拱手作揖,说了一番生意场上例行的客套话,然后不等张秀庭发问就主动告知:“犬子昨晚两时许已经平安回来了。”
这个消息这时已经引不起张秀庭的兴趣了,他需要了解的是具体情况以及朱维鑫为何没立刻主动向警方告知的原因。他压抑住内心的些许不爽,故意用平和的语调道:“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儿?”
据朱维鑫说,情况是这样的——
今晨两时许,轮睡在前面店堂守夜的学徒小丁被一阵儿轻轻的叩门声惊醒,由于白天发生了绑票案,小丁有些害怕。初时没有敢作出什么反应,叩门声停顿了片刻,又响了起来,于是他只好大着胆子起来,隔着门板小声问外面是谁。从外面传来的声音比小丁的还轻,但却腔势十足:“别废话,要小少爷的,赶快去把后门打开!”
小丁吓得浑身颤抖,反应总算还正常,说请稍等,容我报先生去。朱维鑫和妻子因担心着儿子的生死还没休息,闻听消息一个激灵,说这肯定是绑匪来送赎票音信了,赶快照他说的开了后门放他进来。
朱维鑫快步下楼,直奔后院打开了院门。绑匪是划着那条已经出现过的渔船来拜访朱老板的,因考虑到河岸与朱家内宅隔着一个后院,夜半敲门会惊动邻居,故停泊后先从石灰行旁边的小巷里绕到前面去叩店堂门,待等里面应门后又返回渔船上。此刻朱维鑫把后门一开,只见面前站着一个头戴斗笠的黑影。
对方还挺讲礼貌,冲朱维鑫躬身作揖:“是朱老板?久仰!久仰!”然后自我介绍,“兄弟就是‘立早鱼!’”
朱维鑫心里只惦记着儿子,倒已经忘记了害怕:“请阁下进来小坐片刻,吃点儿夜宵。”
对方摆手:“多谢!不必了!”
朱维鑫连连拱手:“不敢动问,犬子……”
“兄弟正为此事而来,贵少爷在我手里,平安无事。朱先生如若把‘神石’交出来,兄弟保证毫发无损地送少爷回家。”
“‘神石’?这是什么物件?”
对方冷笑连连:“看来,朱先生是不想要这个儿子了?废话休说!只问你:交?还是不交?”
朱维鑫不敢回避这个话题了,却换了个说法:“在下知道阁下手头拮据,愿意奉上重金为您解危济难,无论黄金、银洋,抑或其他……”
“停!”对方低喝一声,把朱维鑫下面要说的话吓了回去,随即吹了一声口哨。朱维鑫正犹疑间,从渔船那芦席棚子蒙住的小小船舱里钻出一条黑影,身姿灵活地跳到岸上,朱维鑫忽然发现他的怀里横抱着一个孩子!
这不是儿子还会是谁?朱维鑫紧张之下情不自禁刚要叫喊,“立早鱼”已经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巴:“不许出声!”又是一声口哨,另一位就把孩子抱到近前,手持一把尖刀,在孩子的那张熟睡的脸前晃动了两下,惊得朱维鑫哪里还敢吭声。这时,老板娘也出来了,见状倒抽一口冷气,一个马失前蹄险些栽倒,被朱维鑫赶紧搀扶住。
“立早鱼”也拔出了刀子,对准了朱清霖,悄声道:“我数到三,如若不把‘神石’拿出来,只好血溅当堂了,天亮了你们夫妻俩就操办丧事吧!”
朱维鑫夫妇再也把持不住,立刻跪下,嘴里不敢吭声,只是冲绑匪磕头。但对方不为所动,只管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进行:“一——二——三!”
黑暗中闪着幽光的刀子刚刚举起来时,朱维鑫开口了:“我答应!我答应!”
就这样,“熹宗神石”交给了气焰极为嚣张、竟敢带着肉票直接上门逼着事主赎票的绑匪。
绑匪留下了朱清霖,同时也留下了“敢报案,灭你们全家”的警告,划着渔船迅速离去。朱维鑫夫妇检视儿子,闻到了一股酒气,这才明白儿子为何如此沉沉大睡,原来是让绑匪灌过酒了。他们放心不下,想请个郎中来诊诊脉判断一下看是否有碍,但又生怕走漏了消息传出去惊动了警方被绑匪认为是报案而采取灭门措施。正为难时,忽然想起账房刘先生是懂医道的,于是便差一个学徒立刻去把刘先生请来。
刘先生从家里匆匆赶来后,给犹在熟睡中的少爷朱清霖搭了脉,说不碍事,于是朱维鑫夫妇就放心了。刘先生被老板留了下来,朱维鑫跟其商量此事如何保密,怎样对警方说。两人议了一阵儿,决定警方不来询问的话,就不说;来询问了,就说孩子是绑匪自己将其放回的。反正朱清霖被绑匪灌醉了睡梦中什么也不知道,即使刑警事后要问孩子料想也说不上什么来的。
于是,朱维鑫便把当晚在石灰行里住宿的伙计、学徒还有女佣夏妈都召集起来,让他们一律按统一口径对待刑警,对此事严格保密。
石灰行上下谁也没有料到刑警竟然一夜没睡一直在忙着调查案子,更没有料到专案组组长竟会在石灰行还没开门营业时就已经登门进行第二次调查来了。当然,最出乎意料的是小少爷早晨醒来后竟然精神十足地大叫要吃热干面,从而惊动了张秀庭。刘先生是前清秀才,饱读诗书,后来还参加过辛亥革命,见识过大世面,是一个很会审时度势的人物。另外,他还跟一个老道学过一种不知什么路数的气功,跟人打交道时,据说善于通过对方所散发出的气场判断对方厉害与否。刚才他跟张秀庭一照面,马上感到对方气场甚剧,于是就去跟朱维鑫说:看来此事是瞒不了共产党警察的,先生你还是把情况如实说了吧。
朱维鑫对于刘先生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当下就点了头,于是就跟张秀庭有了这次谈话。
当下,张秀庭听朱维鑫的上述这番陈述,又是吃惊又是后悔,寻思分析案情时已经考虑到绑匪是会把赎票通知传递到石灰行的,当时也已经关照过朱维鑫让其接到绑匪通知后第一时间报告专案组,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没有料到绑匪竟然繁事简做,连通知也不发一道,干脆连夜直接带着朱清霖登门以刀逼着事主赎票。唉!早知道会这样,昨晚留下两人住在石灰行,问题就解决了。
张秀庭定定神,寻思这个案子弄到这一步,还真没有想到。往下怎么办,是继续侦查下去呢,还是暂时停止侦查,得向上级汇报情况后才能决定。当然,作为程序,他此刻得先做一份笔录,另外还得亲眼看一看朱清霖。朱维鑫在作情况陈述时,说了他留心到的一个细节:另一个绑匪的额头上有一条刀疤。
张秀庭忙完这一切后要告辞时,忽然想到绑匪对朱家的灭门威胁,便对朱维鑫说你不必害怕,我去向领导汇报情况后,会作出妥善安排的。人民政府肯定会切实有效地保护老百姓的,共产党说到做到。
张秀庭返回汉阳公安局专案组驻地后,把情况对专案组其他从外面调查完刚刚回来的刑警一说,大家都感觉意外。张秀庭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先去两个人给我把石灰行朱老板一家子保护起来,我觉得这两个绑匪有点儿邪门儿,犯罪思维轨迹有点儿不按常规,万一真的冲朱家人下手,那就不是后悔不后悔的事儿了。于是就派刑警严清忠、戚再生化装后带着手枪前往石灰行,其余人原地待命,张秀庭去向上级汇报情况,听候指示。
武汉市公安总局治安处对于这起案件出现这么一个结果也深感意外,尽管被绑的孩子没有受到伤害,平安归来了,但是事主却蒙受了重大损失。这个结果的性质,说到底等于是案犯登门直接抢劫了“熹宗神石”!同时,由于绑匪的作案手法嚣张,更使人气愤,对于公安方面来说,还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达:窝囊。
因此,领导决定专案组应继续开展侦查工作,一查到底,抓获绑匪,追回赃物,完璧归赵。
张秀庭受了案犯那邪门思维的启发,决定也来一个不按常规出牌,他考虑到要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切实有效地保护朱家人员的需要,决定把专案组移到“朱记石灰行”去办公。
可是,张秀庭刚对专案组战友说了这个决定,大家还没出发前往石灰行的时候,又传来了一个大出意料的消息:朱清霖又被绑票了!
四、再次绑票
朱清霖昨晚被绑匪灌了几口酒熟睡了一宿之后,今日精神很好。早餐吃过热干面,原本是要去上幼稚园的,但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朱维鑫当然不会让儿子出门了。不但不让出门,还指令女佣夏妈寸步不离地守着朱清霖,活动范围限于石灰行。如果发生情况,立刻呼喊。石灰行一位姓王的伙计曾在少林寺习练过武术,拿根木棍儿对付三五人不成问题,朱维鑫关照他做好准备,一旦绑匪再来侵犯的话立刻作出反应。
夏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虽然主人让她今天不必干活,只负责带孩子,但她见女主人操持厨务太忙碌,就主动去拿了一些蚕豆在后院葡萄架下坐定了剥豆瓣,朱清霖则在旁边玩耍。为防止意外,朱维鑫吩咐把后门关上,还上了锁。
但是,仅仅过了一刻钟,夏妈的豆瓣只剥了没几把,女主人颜氏去后院给儿子送零食时,朱清霖已经不见了!不但朱清霖不见,连陪护他的夏妈也没了影子。后院门已经洞开,葡萄架下那个盛放豆瓣的木盆下面,压着一张三指宽的纸条,上书两字——“神石”。
当时,没有发现另外还丢失的东西——后院西侧用于堆放柴草杂物的那间平房门口的鸽棚里的鸽子也被绑匪掠走了。
颜氏大惊之下,放声大哭。朱维鑫等人听见哭声奔进后院,见状一个个呆若木鸡,朱维鑫愣了片刻,惨叫一声,瘫坐地上,随后昏了过去。刘先生懂些医道,立刻掐人中灌凉水,采取了一番措施,方才把他救醒过来。
这时,奉命前往石灰行执行保护之责的刑警严清忠、戚再生刚刚赶到,闻知情况后,吃惊不小,一面布置众人火速沿河打听、寻找,一面找了个有电话的公司往专案组打电话报告。
张秀庭率专案组剩下的三名刑警急急赶到石灰行时,朱维鑫犹是双手捧脸号哭不已。张秀庭看了那张写着“神石”两字的纸条,感到十分奇怪:今晨两点绑匪上门逼着赎票时,朱维鑫不是已经把“神石”交给他们了吗,怎么这会儿再次登门作案,而且一绑就是两个人,仍是点明了要“神石”?他决定跟朱维鑫谈一谈,考虑到保密因素,在征求朱维鑫的意见后,两人进了账房,关上了门,门口还站上了刑警,不许任何人靠近。
朱维鑫冲张秀庭连连拱手:“张同志,这回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只有靠你们警察替我做主了!”
张秀庭让朱维鑫别激动,先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大家商量着看怎样把这个案子圆满办下,这样,“神石”也保住了,少爷和夏妈也保住了。
朱维鑫于是说出了实情:原来,今晨绑匪前来赎票时,他交出去的是一块假“神石”。这块假“神石”,还是他父亲随同真“神石”一起留下来的。因为父亲担心世道混乱,会助长歹人图谋“神石”之心,为防万一,就请了一位湖南匠人按照他提供的图纸,仿制了一块假“神石”。此事父亲一直没有吐露过,直到临终前把“神石”传给朱维鑫时,方才一并交待。朱维鑫对此自然也是守口如瓶,对包括妻子颜氏在内的所有人都严守着这一秘密。时运不佳,父亲的担忧竟然果真变成了事实。朱维鑫在惊恐之时想到幸亏父亲生前有了这一安排,心思总算稍稍定些,寻思用赝品把绑匪打发了吧。
因此,朱维鑫其实对于绑匪的主动登门强逼赎票是怀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的。他用假“神石”赎回儿子后,担心的倒并不是这招“狸猫换太子”的把戏会被绑匪识穿(尽管他此刻不得不怀疑当初老爸所雇请的那位湖南师傅的造假能力和老爸的验收标准),而是生怕绑匪的“报案灭门”威胁会引来麻烦。但是,跟刘先生商量下来,这件事是无法向警方隐瞒的,再说,说到底当然还是警方将绑匪抓获最为稳妥。所以,他向张秀庭道出了赎票情况。只是,此刻他后悔的是:他不该隐瞒对绑匪玩了“狸猫换太子”的把戏。
张秀庭听朱维鑫如此这般一说,真有一股指着对方大骂一顿的冲动: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啊,用假石赎回了人质,然后在石灰行这边组织蹲守,待绑匪二次登门作案时将其拿下!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就因为石灰行老板自以为是的精明而白白丧失了。往下应该怎么破案?他此刻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
结束了跟朱维鑫的谈话后,张秀庭跟副组长徐春薪交换了意见。徐春薪是刑警出身,后来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因为暴露了身份而离开了国民党警察局,去外地从事地下交通站工作。武汉一解放,他就奉命返回汉阳公安局,还没安排职务就被抽调到专案组来了。徐春薪的特点是耐心细致,考虑事情很是周密。现在,徐春薪用这一思维特点对待眼前的案情,跟张秀庭三言两语就定下了侦查思路。
这个侦查思路是:既然朱家对于“熹宗神石”这个秘密藏得那么严实,到朱维鑫这一代之后,经历了军阀、“中统”、日寇、“军统”的纠缠都没有暴露出来,为什么会被绑匪“立早鱼”轻而易举一下子就摸清了底细,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就贸然下手而且一举成功呢?从“立早鱼”的作案过程来看,这显然是一个有着丰富江湖黑道经验的匪盗分子,也就是说,“立早鱼”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是不会贸然下手的,否则,就会把事情做拙,不但达不到谋取“熹宗神石”的目的,而且对于像他那样一个可能在江湖黑道上有点儿名气的人物来说,还是一种有损名誉的行为。他显然是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的。所以,现在暂时先可以把其他途径放到一边,而盯着“立早鱼”是如何得知朱维鑫手头确实有“熹宗神石”这一点去调查。相信在这方面一旦取得突破的话,离此案的侦破可能也就不远了。
张、徐两人议定之后,立刻对如何调查作了布置,全组六名刑警,分别对包括朱维鑫夫妇、账房刘先生以及其他伙计、学徒进行了询问,结果就冒出了一个人来。
冒出的这位兄弟此刻不在“朱记石灰行”,但他在武汉,在汉口的一个建筑质量很好的地方太太平平地待着。这个处所戒备森严,门口有人持枪站岗,外人是不能随便出入的,如果不应该出入的人硬要出来或者进去,岗哨就会开枪,格杀勿论!这位兄弟当初住进去时,这个处所的大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书:湖北省汉口市警察局看守所。武汉解放后,牌子已经换了一块:武汉市公安总局汉口公安局看守所。
朱维鑫的妻子颜氏有个嫡亲侄子,名叫颜寻至,二十一岁。颜寻至原是武昌那边一家酱园的学徒,快要满师时不知是脑子进水了呢还是哪根筋出了毛病,竟然跑到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新兵征召处,主动提出要求参军入伍。这时候正是共产党刘邓部队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当儿,国共战争已经呈现出对国民党一方不利的态势,国民党政府的征兵工作发生了困难,已经在抓壮丁了。现在有人主动上门要求当兵,人家真是求之不得。在验证过颜寻至没有精神病之后,马上收下了他,立刻委任他担任副班长。
据颜寻至后来透露,他是想上前线打几仗后,当个军官,慢慢升到将军,好光宗耀祖。结果进新兵营受训时,方知这种苦头比他在酱园当学徒还不知苦了多少倍。于是,颜寻至就利用新兵营长官因为他是主动要求入伍的原因而对他的那份信任,悄然不辞而别。颜寻至逃回武汉后,仍想去武昌的那家酱园继续他的学徒生涯,但酱园老板告诉他警备司令部已经来人警告过了,让一见到他就扭送过去。估计即便不枪毙,也得脱掉一层皮,掉下半扇子肉,让他还是远走高飞吧。
颜寻至想了想,当然也不敢回武昌县乡下老家了,于是就到“朱记石灰行”投奔姑姑。颜氏只有这么一个侄子,自然不能拒绝,跟朱维鑫一说,朱维鑫尽管对颜寻至没有好感,但老婆的这个面子总得给的,于是就点了头。不过,朱维鑫像是有先见之明似的,说“朱记石灰行”是不能留逃兵的,回头警备司令部找上门来,我吃不了得兜着走哩。这样吧,他在酱园干过,又当过兵,看来力气是有一些的,我把他荐到一位朋友开的碾米厂去做工吧。
于是,颜寻至就去了碾米厂。他在那里干得倒还不错,深受朱维鑫的那位老板朋友的喜爱。每次见到朱维鑫都说老兄我得谢谢你啊,你给我荐来了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可是,今年四月间这个“不错的小伙子”就做出了错事:他在喝酒时跟人争吵,双方动手打了起来,结果他一拳将对方打倒,直接去了阎王爷那里,于是就被国民党汉口市警察局逮了进去。一个月后武汉解放,共产党政权接管了警察局,将看守所内关押的人犯进行了甄别清理,释放了一部分。而颜寻至犯的是人命案子,所以没有被释放,继续关押,等待处置。
那么,颜寻至跟眼下的这起绑票案有什么瓜葛呢?问题在于:朱维鑫持有“熹宗神石”,“朱记石灰行”包括刘先生这样深受老板信任的高级伙计也是不清楚的,最多听过传说,传说当然不能代替实际。“神石”的存在,只有朱家人才知道,而且都亲眼看见过,不过包括朱维鑫本人在内,一年也只有一次机会才能看到。那是大年三十祭祖的时候,“熹宗神石”必被高高供奉于中间,和祖宗牌位一同接受朱家人的叩拜。颜寻至是单身汉,过年时碾米厂放假,他是应姑姑之邀到朱家这边来度假的。因为是女主人的嫡亲侄子,朱维鑫也就把他视为自家人,祭祖时没让他回避。当然他是没资格参加仪式的,连动手相帮的份儿也没有,唯恐祖宗见怪。
但是,颜寻至因此而成为亲眼看见“熹宗神石”的唯一一位外姓人。
朱维鑫夫妇在分别接受刑警调查时都道明了这一点。当然,在这对夫妇看来,颜寻至应该是没有瓜葛的,因为他关在看守所里,自古以来不是一直说“狱不通风”吗?他在里头待着还能怎么着?
可是,专案组诸刑警可不是这么考虑的,他们是知道看守所是否“狱不通风”的。颜寻至还在里面关着没错,可是,他人是被关着,思想可没关着,嘴巴也没关着。一伙原本不是善茬儿的家伙在监房里整天待着,还不闷得发慌,只怕连哑巴也会有吼几声发泄发泄的念头。所以,他们互相之间肯定会用闲磕牙瞎聊天来打发时间,这一闲聊瞎侃,谁能保证颜寻至管得住自己的嘴巴不把“熹宗神石”的秘密透露出去?
张秀庭便说赶紧派人去汉口看守所找颜寻至了解吧,看他对谁透露过“神石”之事,如果透露了,听过他这条消息的人犯此刻是否仍被关押在里面?如果有人已经释放了的,那就得一个个盯着追查下去!
刑警刘继、戚再生、关度三人于是便奔汉口公安局看守所,把颜寻至从监房里提出来一问,还真估料得没错,这主儿确实在监房里闲着没事和众人犯胡吹神侃时把朱维鑫家的那块祖传宝贝“熹宗神石”透露出去了。
几时吹出去的?
这个,让我想一想。颜寻至扳着手指头算了算,说好像是五月上旬的事儿吧,也可能是过了五月十号的。你们不知道,在里头待着,对于日期没有那么个灵性,谁记得那么准?记准了又有什么用?反正是解放前的事儿了。
颜寻至说得轻松,刑警可就紧张了,因为解放后看守所是释放出去一大批人的,这将会给调查增加难度,而且很有可能“神石”信息就是这么泄露出去后才导致发生这起绑票案件的。于是就让颜寻至再想想,颜寻至说肯定是解放前的事。
既然是解放前透露的,那就说说当时跟你关在一个监房里的人犯吧,一共关押了多少人,都有谁谁谁,一个个都说一下,不能遗漏!
可是,颜寻至却摇头。不是拒绝,而是无法满足刑警的要求。为什么?监房里关着的人犯使用的都是编号,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他根本不知道。
不过这也难不倒刑警,他们随即去找了所方,查阅了关押记录。最后,弄清楚一共有四名人犯具备既是颜寻至当初的听众又已经释放了的条件。
这四名曾与颜寻至蹲过同一个监房的人犯的情况如下——
包大根,二十三岁,汉口人,以行乞为生,居无定所。武汉解放前两个月因故意弄脏一位国民党将军太太的衣服而被巡逻宪兵扭送至汉口市警察局看守所关押。像包某的这种情况当然是无法立案的,但因为是宪兵送来的,警察局不敢立刻释放,结果一关就关了两个多月。武汉解放后第三天,军管人员在甄别在押人犯情况时,只看了卷宗中那张收押登记单子,就把包大根的姓名圈了出来,当天下午就释放了。
蒋起早,三十六岁,武昌县人氏,地痞,单身汉,住武昌落叶巷11号。武汉解放前一月受某方指使,纠集地痞十余人在汉口市一家饭庄寻衅闹事。该饭庄老板与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一将级大特务是亲戚关系,遂报警察局处置。警察局知道指使制造事端的某方势力也不好惹,不敢过分得罪,于是就采取变通措施,只逮了为首的蒋起早。逮进来后也没有立案,估计是想关几天就释放的,但因为时势紧张,经办人员自己盘算出路都来不及,结果就把蒋给忘记了。解放后军管人员甄别时,就把蒋起早释放了。
邹金发,十七岁,汉口人,无业,其父是开南货店的,住汉口千波街槐树巷。小学毕业后,长期混迹闹市,结交不良少年,屡屡偷窃,曾多次被警察局拘留。武汉解放前一周,在汉口大兴百货公司扒窃时被事主当场抓获。百货公司方面恼于其行为影响该店声誉、生意,遂将其送交汉口市警察局要求关押。武汉解放后,邹金发与包大根同时被释放。
姚秋生,三十四岁,武昌县人,渔民,居无定所,以渔船为家。1948年8月因被疑参与水上打劫杀人遭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通缉,1949年3月中旬在汉口市被市警察局刑警在对旅馆进行例行巡查时发现,当场拘捕。警察局通知警司侦缉大队递解,侦缉大队派员前来提审过姚,因无口供而未将其移押。其时局势动荡,侦缉大队已经无心办案,而汉口市警察局既对姚没有兴趣,也没有管辖权,也就将其搁置一边不予过问。武汉解放后军管人员甄别清理在押人员时,将姚秋生释放。
刑警在抄录四人的相关情况时,看守所值班警员正好办理交接班,接待他们的那位姓姜的内勤警员向前来接班的警员李志尧介绍了刘继三人的身份和来意,让其接替他继续协助刑警办理调查事宜。李志尧问明刑警是来调查什么事情之后,对三人中负责的刑警刘继说:“巧得很,这件事我倒也有一个线索可以向你们提供。”
刘继大感兴趣,连忙递过去香烟:“多谢,请说!”
李志尧告诉刑警,关于颜寻至在监房里吹牛说到“神石”之事他也听说过,不过他不是听颜寻至说的,而是听一个姓薛的人犯说的。那个姓薛的人犯不过十五岁,因偷窃被原国民党汉口市警察局拘捕。本来,像这种小偷儿最多关上半月一月就该释放了,否则看守所就得人满为患了。但是,这个人犯以前在理发店当过学徒,会理发,还会敲背、掏耳朵,看守所一班警察需要他伺候,连刑队那些家伙也经常来借光。所以,这个人犯就一直关着没有获释。当然,他在看守所是受到优待的,伙食比其他人犯好些,还有一定范围的行动自由。像这种小偷儿出身的机灵鬼,在这种环境中当然能够找到自身最大的价值,他就不时替那些需要传递什么的人犯偷偷效劳,以获得一些零花钱;同时,也利用跟各类人犯打交道的便利,捎带着替所方和刑队收集些情况,悄悄报告上来。“神石”的话头就是他向当日当差的李志尧报告的,不过他不是报告颜寻至说了些什么——这是不值得报告的,而是听那个被人犯称为“老强盗”的姚秋生说的,当时姚听后在放风时对其他人犯说过一句:“那块石头很值钱的,有机会可以弄来看看!”
刑警一听大为兴奋,便问那个姓薛的少年人犯呢?李志尧说他是第一批获释的,早就出去了。
刘继三人带着上述调查情况返回“朱记石灰行”专案组临时驻地,向张、徐两位组长汇报后,张秀庭马上说:“还等什么,先去找那个叫姚秋生的家伙!”
徐春薪点头赞同,说这姓姚的是渔民出身,又曾被怀疑参与过打劫杀人犯罪,又知晓“神石”情况,还扬言有机会要弄来看看,这就值得怀疑了。这样吧,我去寻这小子!
张秀庭于是就指派关度、刘继和徐春薪去寻找姚秋生,这边他和刑警戚再生去寻访另外包、蒋、邹三个榜上有名的主儿。石灰行这边,留下严清忠镇守。严清忠是武工队出身,为人机警,有战斗经验,让他保护朱家一帮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五、绑匪失约
徐春薪、刘继、关度三人根据看守所方面提供的姚秋生的相关情况,对姚秋生获释后的行踪去向进行了分析,认为像这种主儿,不论他是否涉及“神石”绑票案,老老实实回到武昌县乡下去打鱼那是不现实的。今年三月间国民党汉口市警察局抓到他时,他就是在汉口的一家旅馆里住着,所以,这个人不大可能回到打鱼为生的老路去的。
那么姚秋生会干什么呢?刑警根据他们对这类家伙的习性判断,姚秋生多半还在武汉三镇混着,而且,他必定有一帮称兄道弟的朋友。以其在黑道上的作用,估计不过是做做马仔混口饭吃吃的份儿。而如果绑票案与其有关,那则是他把颜寻至在看守所透露出来的关于“神石”的消息提供给了其中的某人。然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某人采纳了姚秋生的劫取“神石”的建议,自行安排布置了绑票案;另一种是不但采纳姚秋生的犯罪建议,还邀其合伙同干,估计渔船、“立早鱼”之类的绑匪就是他物色联系的。
根据上述分析,刑警认为要迅速捕捉到姚秋生的行踪线索,只有从黑道上去想办法。于是,徐春薪就对关度说:“老关,这件事看来得请你费神了。”
之所以有这话,是因为关度是原国民党汉阳警察局的老刑警,解放后军管组接管时根据旧警察在解放前的一贯表现,留用了一部分人,关度是其中的一个。徐春薪也是干过旧警察的,他知道吃这碗饭的刑警只要干的时间稍稍长些,为了刑事侦查的需要,每个人都会物色一个或者数名江湖黑道上的喽啰,作为耳目使用。而关度是有着二十年警龄的老刑警,所以,徐春薪认定关度手头肯定掌握着若干名耳目,此刻发挥他的作用是最有效的。
果然,关度让徐春薪、刘继在一家茶馆里坐着喝茶,他自己出去只转了半个小时,回来后就说已经布置下去了,我们就在这里喝着茶等候消息吧,最多两个小时,就会有姚秋生的消息报过来的。我还顺便让他们打听江湖上是否有一个诨号“立早鱼”的家伙。
三人只喝了两碗茶,抽了一支烟,耳目就来报告消息了:“立早鱼”这个名头武汉地面上没有人听说过,姚秋生这人倒已经打听到了,最近他在武昌丁字桥一带频频露面,每天下午都去“昌盛茶楼”喝茶,有几个固定的道上朋友在一起,其中有一个黑大汉看上去蛮有市场的样子,手里转着两个实心钢球,肩膀上架着一只猴子。
刑警一听有猴子,马上想起绑票案中曾经出过场的那个动物演员,顿时振奋。三人议了议,决定立刻去武昌丁字桥那里查访,既然姚秋生在那一带出入,那看来多半是住在那边的,准备多费点儿劲儿,料想是能够查得到的。
到丁字桥后,刑警先打听“昌盛茶楼”,入内占了一副能够观察到进出茶楼的每一张脸的座头,要了茶水,慢慢地喝着。一碗茶还没有喝完,就看见一个又高又大的黑汉,手里把玩着一对钢球,肩上蹲着一只脖颈上拴着细铜链的猴子,一步三摇大模大样地进了茶楼。
跑堂迎上前去招呼:“马二爷您老来啦!有三五天没光顾敝号了,我还以为您外出访游去了呢,楼上请。还是喝龙井明前?”
黑大汉点头粗声道:“是的,这几天,姚秋生他们来过吗?”
“有两天没来了,不知今儿个来不来。”
“不管他们,我只管喝茶。没人说话,正好图个清静。”
徐春薪听了这番对话,心里马上作出判断:这个黑汉子应该跟绑票案没有关系!这是因为他跟姚秋生已有数日没有见面了,这应该是真的,因为他不可能知晓此刻眼皮底下待着三个正调查他们这伙主儿的刑警,而故意借着跟跑堂说话的机会传递伪造的信息;此外,如果他参与了绑票案,那么就不敢把这只猴子还像往常那样放在肩膀上公然招摇街头了。
徐春薪飞快地跟刘继、关度交换了一个眼色,那二位也是这么想的,当下立刻会意。三刑警目送着黑大汉上楼后,悄声商议接下去应该如何。最后决定由一人出面通过茶楼老板约谈黑大汉,从他那里查摸姚秋生的下落。
这事儿由熟悉市情的关度去做最合适了。老刑警向跑堂问明老板姓隋后,就去后面老板室拜访。用《沙家浜》里阿庆嫂的话来说:开茶馆,盼兴旺,江湖义气第一桩。由此可以想象,茶馆老板通常都是熟谙道上那一套的,否则只好改行了。此刻这位隋老板也是这样,一看关度出示的证件,马上点头哈腰极尽客气。关度说隋老板你不必忙这忙那,单忙一桩就可以了,我想请教一下:外面靠窗口坐着的那个黑汉子,手里玩钢球、还带着一只猴子的那位,你知道是什么人吗?
隋老板一听就说知道,这是马二爷,叫马江村,他是青帮的,又是粪把头,在丁字桥一带很有名的。
关度点头:“行了!这样,麻烦隋老板把这位马二爷叫到这里来,我想跟他单独谈谈。”
马江村立刻来了,这人给关度的印象是有些豪爽,而且也很识时务,听说要了解姚秋生,马上把他所知道的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包括姚秋生最近下榻的地址,就在丁字桥附近的三珠巷。
于是,刑警就知道姚秋生前些日子确实频频跟两个陌生汉子交往,不知在商议些什么,好像是在谈合伙做一笔生意。
徐春薪、刘继、关度三人商量后,决定立刻前往三珠巷跟姚秋生当面接触,盘问下来感到可疑的话,干脆带走。
后来知道,三珠巷这边是姚秋生姐夫的一处空宅,他在被国民党汉口市警察局拘捕前就已经入住其内了。获释后,又回到三珠巷原处住下。那是一套面积不大但带有院子而且有前后门户的宅院,刑警登门时,前面院门虚掩着。推门而入,迎面正房的门内坐着三个男子,正抽烟喝茶聊着什么。姚秋生眼力不错,刑警尽管穿着便衣,手里也没有手枪、手铐,但他竟然一眼就断定这是便衣警察,而且是来跟他过不去的,当下二话不说,一跃而起,转身就往后门那里跑。
徐春薪断喝一声:“站住!”随即亮出了手枪,枪口朝上扣动了扳机。枪声使姚秋生吃惊不小,脚步停顿了一下,被刘继冲上前去制服,铐上了手铐。
另外两个家伙也被关度掏枪逼住,一并拿下。随即对住所进行搜查,搜出单刀一把、匕首两把。那时还没有“管制刀具”一说,所以这算不上违反了什么。
当然,没有搜查到赃物并不能证明姚秋生是清白无辜的,见到刑警连话也不说拔腿开溜一举本身就是可疑情形了。当下,刑警将被捕的姚秋生三人押解到就近的派出所,立刻分别讯问。
讯问的结果似乎颇具戏剧性:绑票案专案组三刑警简直哭笑不得,而派出所和武昌公安局相关警员却是额手称庆,对徐春薪三人连连作揖道谢。
原来,姚秋生和那两个同伙两天前确实干了一起刑事暴力案件,不过不是绑票,而是蒙面抢劫了武昌“大泰布店”,不但抢了当天的全部营业款,而且还把该店最好的三匹丝绸一并劫走。三人作案后,担心被警方怀疑,所以未将赃款赃物带回家,而是悄悄藏匿于乡下一座破土地庙里,想等到风声过后再分赃。没有料到今天刑警突然登门,姚秋生做贼心虚想逃了再说,哪知反倒使罪行得以暴露。
徐春薪三人白白辛苦了一番,难免带着点儿沮丧神情返回“朱记石灰行”。张秀庭和戚再生也刚刚返回,他们分头对看守所提供的另外三个已经获释的人犯包大根、蒋起早、邹金发作了当面查摸,已初步证实这三人并无作案嫌疑,也没有向其他人说起过颜寻至在看守所里所说过的朱家的“熹宗神石”之事。按理说来,张秀庭、戚再生二位也应该跟徐春薪三人差不多,显出些许沮丧神情才是,但此刻在徐春薪三人眼里,这二位却显得容光焕发,像是已经掌握到了很有价值的线索似的。这应该怎么理解?徐春薪朝张秀庭投以询问的眼神。
张秀庭马上读懂了这个眼神中所兜着的那个问号,一言不发地把一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徐春薪的面前。
这样东西真的只能小心翼翼地对待,因为它实在太小了,不但小,而且很脆弱,一不留神没准儿就给弄坏了。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张极薄极软、只有二寸长寸许宽大小的纸,上面用铅笔写着蝇头小字:晚九点朱一人将神石送铁门关,验后交人。
徐春薪见之一个激灵:“绑匪让赎票?”
这张纸条是在中午时分出现的。前面说过,上午发生绑票案件时,朱家后院鸽棚里的那几羽鸽子也给绑匪顺便掠走了。但当时处于这等混乱的情势下,根本没有人留意到。这几羽鸽子平日是归学徒小徐喂养的,过了一会儿,他想起应当喂食时去后院方才发现鸽子已被绑匪掠走了,于是就报告了朱老板。朱维鑫担心儿子的安危都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了几只鸽子,当下只想是绑匪抓鸽子去杀了当下酒菜的,随口骂了两声。中午,石灰行开饭了,朱维鑫哪里吃得下饭,考虑到自己不吃的话,家人、伙计肯定也不大敢吃,于是就借故回避,去了后院在葡萄架下捧了一杯茶水发呆。一会儿,忽然听见头顶上方传来鸽子叫声,还没回过神来,一羽鸽子已经飞掠而降,直扑鸽棚。朱维鑫一阵惊喜,马上叫小徐来看。小徐喂养鸽子多时,对鸽子已有感情,当下就轻轻捧住了鸽子检查是否受伤了。这样,就发现绑在鸽子腿上的纸条了。
朱维鑫把纸条送到留守刑警严清忠手里,严清忠看过之后,安慰朱维鑫说不要着急,绑匪既然让赎票,那说明少爷和夏妈眼下还是安全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解救两人的机会。等我们那几位同志回来后,容再计议。反正绑匪约的时间是晚上九点,来得及作安排的。
张秀庭返回后,严清忠把这张纸条交给专案组长,张秀庭的观点跟严清忠是一样的,现在徐春薪三人也回来了,专案组正好开个短会研究此事。鉴于此事得由朱维鑫亲自出场,所以专案组把朱老板也请了过来。
众刑警和朱维鑫一致认为应该趁此机会前往铁门关解救人质,捉拿绑匪。这个主意看来没错,但鉴于绑匪之前曾经有过“报案灭门”的威胁之词,所以得防止这是一个调虎离山之计,把专案组调离石灰行后向正主儿扑过来下手。这一点,必须得提防着。因此,得在石灰行这边留下两人承担保护之责。同时,还要考虑到朱维鑫携带“神石”前往铁门关途中的安全。如果绑匪在途中进行拦截,害了朱维鑫后劫走“神石”,那对于专案组来说就是彻底失败了。
因此,专案组考虑了一个方案:另外调派若干名刑警,化装成三轮车夫和路人等,将朱维鑫平安送到铁门关。然后,这几名刑警就作为外围二线力量在铁门关预定的位置设伏,协助一线的专案组刑警擒拿绑匪。
最后,就是了解铁门关现场的地形情况了。刑警戚再生家住铁门关所在的洗马长街,从小就在那条街上生活,所以立刻就画了一份现场平面图供大家查看。
洗马长街如今犹在,位于武汉市汉阳区东北隅,东依长江沿江而行,北起晴川路,南抵长江大桥桥墩下,约有五百米。该街成于明代末年,西面是龟山,东面是龟山余脉禹功矶,街面从龟山颈子上碾将过去,意图很明显:“龟断颈,蛇断腰”,使龟山身首分离,断其龙脉。这样一来,洗马长街就与当年建在蛇山腰上的黄鹤楼隔江呼应。
洗马长街之名,得名于禹功矶边上的古迹“洗马洞”。而“洗马洞”又与另一历史名人有关:传说关羽屯兵汉阳时常来此处江边遛马、洗马。这个如今无处可寻的洗马洞,成了此街名称的来由。
再说铁门关,那是洗马长街上的一座大门。这个军事要塞建于三国时期,在古汉阳是城东北的唯一通道,也是商贸要道。明末,铁门关毁于战火,清代在铁门关遗址上建关帝庙,祭祀关公,后一同被毁。1990年,当地政府重新修建了现在的铁门关。因此,在本案发生时的解放初期,铁门关只是作为一个地名存在于武汉人的生活中。
洗马长街靠近长江的一侧,如今谓之“滨江大道”——就是汉阳江滩公园。在本案发生时,这一带都是民居,直到1954年长江发大水后,政府鉴于安全原因决定全部拆除,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滨江大道这块地盘。
当下,专案组诸刑警连同朱维鑫一起看了戚再生所画的这份平面图,对朱维鑫过去后的行动作了安排:见到绑匪(或者绑匪派来的代理人)后,可以先给对方看看带去的“神石”,但是,不能交给对方,要咬住一条:不知人质生死,所以一定要确信人质安全后才能交出“神石”。绑匪可能对这个说法没有思想准备,即使有准备估计也不大可能带着两名人质到现场,因此会在纠缠、威胁一番后被迫作出让步,或去请示正主儿(如是代理人出面的),或去跟同伙商量,也有可能改期;如果绑匪坚决不肯让步,为保朱老板安全,可将“神石”交与对方。总之,绑匪肯定要离开现场的,届时隐藏于现场民居内的便衣刑警就可以跟踪。当然,如果绑匪是带着人质来现场的,那就直接下手逮人了。
一切都计议停当后,专案组就去借调人手,朱维鑫这边也做了准备。当晚八点半,朱维鑫就乘坐了一辆由化装的刑警踩着的三轮车前往铁门关。另外两位刑警则化装成平民的样子,骑着自行车一前一后保持着几十米距离不紧不慢地悄然保护着朱维鑫。到了洗马长街,三轮车在铁门关停了下来,三名便衣就进入了预定的二线位置蹲守。此时专案组四名刑警早已进入现场,隐藏于四处民居内,对朱维鑫所在的位置形成合围之势。
刑警抱着志在必得之心,牢牢地盯着目标应该出现的位置。九点钟很快就到了,绑匪没有出现。
等了半个小时,绑匪仍然没有出现。专案组四刑警此刻还不知道,“朱记石灰行”那边已有骇人的消息等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