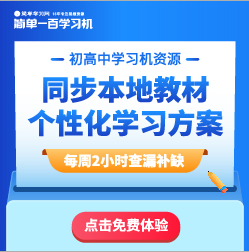十、青楼女特工
尹关先落网后,因涉及特务案件,先是被北四川路公安分局郁局长下令单独关押,当天晚些时候,分局奉命将该案移交市局政保处,尹关先也被移押至市局看守所。他是被作为敌特要犯对待的,有专人负责看押。面对裴云飞、张伯仁的二次提审,状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裴云飞对此感到不解:“见到我们你好像还挺高兴,怎么想的?”
尹关先呵呵一笑:“不瞒二位,我以前跟警察局打过不少交道,东洋人的宪兵队我也进去过,知道办案的规矩:被抓之后,如果承办警员调换,那就意味着情况不妙,要往严里整了;承办员还是原来的,那就好,说明案情不重。您二位这是第二次审我了,没换别人,那说明我的案子还算轻的。”裴云飞心里嘀咕,这可大错特错了,不过既然他有这样的想法,也好,就顺着这家伙的思路跟他聊吧。
“老尹,我们两个今天过来,严格点儿说,也算不上提审,你看我们连笔录都没做,是不是?不过,这也并不是说你老尹的案子就不严重。就拿你过去的那些事儿来说吧,既是盗窃惯犯,又跟国民党特务有勾结,真要严办,判你十年八年算客气的。但话又说回来,那都是解放前的历史问题,我们没发现你在解放后作过什么案子,除了这次被特务分子利用,潜入甜爱路36号甲。公安机关的政策你肯定听说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减轻处罚的机会……”
说到这儿,裴云飞故意停顿下来,引得尹关先一对眼珠子滴溜溜乱转,两片嘴唇微微嚅动,忍了又忍,终于把“是什么机会”的话头咽了回去。张伯仁适时掏出香烟,先给裴云飞递了一支,两人点燃香烟抽了两口,老张这才像是突然想起似的,又点了一支送到尹关先嘴里。尹关先贪婪地连吸数口,壮起胆子:“报告政府,敝人愿意用实际行动争取减轻处罚!让我做什么,请尽管赏示,纵然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那好,我们跟看守所说一下,给你纸笔,你写一份决心书,先表示个愿意改造的态度。你可要认真对待,这是要放入卷宗的,是结案时对你从宽处理的依据之一。”
“我一定认真写……”
裴云飞、张伯仁装模作样站起来准备离开,张伯仁忽然“想起”一件事,对裴云飞说:“上次那份笔录送上去后,领导说那个传呼电话的事还不够清楚,既然过来了,要不要顺便问一下?”
“对啊,你不说我还差点儿给忘了。”裴云飞重又坐下,“老尹,上次提审时你说的那个‘军统’特务屠世臻。和你见过两次面,一次是10月18日晚上在‘新都溜冰场’门口,然后你们俩去了旁边的咖啡馆。另一次是第二天下午,一个女子打了你家弄堂口的传呼电话,通知你去头天那个咖啡馆和屠世臻见面,是这样吗?”
昨晚专案组分析案情,都认为查清屠世臻打电话的位置是关键。麻烦的是,解放前上海市的电话公司,有原公共租界的英商、美商电话公司,原法租界的法商电话公司,也有民国政府开办的国资电话公司。上海解放后,这些电话公司逐步由新政权接管,到本案发生时,已成立上海市电话局(如今上海电信的前身),但使用的设备还是原来的。这些设备分别是英、美、法、德、日五个国家生产的,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施经济和技术封锁,这些不同国家生产的设备无法整合成一个通信网,这就导致了一个难题——无法追查主叫号码的位置,哪怕是市电话局对此也束手无策。裴云飞、张伯仁前来提审尹关先,目的就是想从该犯口中得知更多的细节,指望能发现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找到屠世臻的藏身处。于是,一老一少两个侦查员就合演了这么一出戏。
尹关先脑子里只想着如何能够获得从宽处理:“您二位问的是屠世臻给我打传呼电话的事儿?让我想想………”
尹关先这一想,还真想起了一个细节——那天他原以为打来电话的是屠世臻,谁知对方是个听上去三十多岁粗声粗气的女声,对方打电话的环境也有些嘈杂,隐约能分辨出“削刀磨剪刀”的吆喝声。说了上述这个细节后,自觉于警方寻找屠世臻的踪迹没什么帮助,心里还有一种“过意不去”的歉意,苦思冥想一番又补充说:“那磨刀师傅是一副公鸭嗓子,不知对你们是否有用?”
一声“削刀磨剪刀”的吆喝,对于寻常案件的调查不会有什么帮助。单凭这一声吆喝在全市上千个传呼电话亭周边查摸线索,那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通常领导也不会同意这么干。但对于一起涉敌特案件就不同了,这种耗费肯定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
当天下午,专案组以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的名义向全市二十个公安分局发出指令,要求迅即布置各分局下辖的派出所对各自管段内的传呼电话亭进行秘密查访,寻找一个沿街招揽活儿的公鸭嗓磨刀匠。
这一步走对了。当晚7点多,访查结果陆续反馈回来:全市共有三个符合排查条件的目标,这三人都是苏北扬州人,平时穿街走巷途经的传呼电话亭有十三处。
划定了范围,接下来的工作就需要专案组自己做了。这最后一步调查,耗费了三天时间,至10月31日傍晚,终于确定了那个主叫电话的位置。该电话亭位于长宁路一个名叫“一如里”的弄堂口,在上海市电话局的传呼电话分布图上,它的标号为“0171”。据电话亭老爷叔回忆,那个电话是一个名叫王桂花的无业女子前来拨打的。
时隔十三天,来打电话的人不计其数,老爷叔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这其中是有缘由的——王桂花还真是一个让邻里过目难忘的女子。
王桂花时年三十岁,浙江嘉兴人氏,幼年时就被带到沪上一个经营南货店的人家做童养媳。“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她正要与南货店老板的儿子成婚,战事突然爆发,夫家决定推迟婚期。本以为这场战事时间不会太长,哪知到11月中旬,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队败退。为配合陆军扩大战果,日军战机纷纷出动,飞临上海华界上空投掷炸弹,机枪扫射。王桂花夫家的南货店被一颗炸弹砸个正着,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全家人只有奉婆婆指派去米店籴米的王桂花幸免于难。
命保住了,可赖以生存的南货店却没了。随着日军长驱直入,华界全部沦陷。王桂花逃入法租界,身无分文,只有行乞为生,待交通恢复后再回嘉兴乡下娘家。叫花子做了没几天,一个不慎,着了人贩子的道儿,被卖到四马路一家妓院做了妓女。
王桂花说话粗声粗气,长得倒还是有几分江南女子的俏丽相的。她是被人贩子卖到妓院的,所以是“死契”,没少挨过老鸨的打骂。不过,两三年后老鸨就不敢碰她了——她结识了一个“七十六号”的汉奸特务。这个特务绰号“歪鼻头”,战前是青帮分子,十六铺的职业流氓。这种双料角色,老鸨当然是得罪不起的,王桂花被“歪鼻头”看中后,不用人家发声,老鸨就不敢为难她了。
前面说过,当时活跃于沪上的各路国民党特工是把青楼行院作为理想活动场所的。王桂花跟“歪鼻头”有了交往,“军统”方面即将其列为发展对象,以便通过王桂花从“歪鼻头”那里刺探情报。王桂花的想法很简单,民族大义什么的她根本不在乎,她关心的一是保全自己的性命,二是尽可能多地获得钱财,为自己赎身。如此,“军统”那边没费多大力气,就把她发展为临时工。
王桂花从“歪鼻头”那里获得了不少情报,终于引起了对方的怀疑。好在“军统”认为留着王桂花还有用,“歪鼻头”还没来得及跟王桂花摊牌,就被“军统”行动特工在外滩击毙了。
王桂花得以继续为“军统”效力,她的临时工组织关系转到了美男特工屠世臻手里,接受屠世臻的领导。这妇人天资一般,严格说并不是干特工的料,即使是让她干临时工也有点儿勉为其难。但王桂花有一个优势,她知道自己脑子笨,也从不自作聪明,屠世臻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怎么干就怎么干,从来没有“我想”、“我以为”之类的念头,这让屠世臻比较满意。
抗战胜利后,屠世臻离开上海前往海外前夕,向上级递交的工作汇报中特意提到了王桂花,建议可以根据这个女人的性格特点安排一些活儿,相信她能胜任她非常听话,只要指示准确得当,就不会发生意外。这在特工术语中被称为“行为可靠”,相比于“信仰可靠”、“思想可靠”、“性格可靠”、“技能可靠”等,这类特务适宜从事最低级的活动。别小看这种“低级”,有些时候,所谓的“高级”特工还干不了这些“低级”的活儿,比如常年累月化装乞丐、囚犯 ,当然也包括妓女,进行没有期限的枯燥潜伏之类。
屠世臻是实战经验丰富的资深特工,他的建议,上级自然要认真考虑。不久,上级派员在王桂花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了一番秘密考察,认为基本合格,遂以已去海外的屠世臻的名义每月给她一份津贴,却从来不给她派活儿,留待需要的时候再动用。
王桂花拿着“军统”(稍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津贴,继续从事其青楼行院的第一职业,过着与其他烟花女子相同的日子。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着手对妓院的改造,打击了一批勾结国民党特务、日伪汉奸从事反革命活动,以及剥削欺压残害妓女的恶霸老鸨,废除“卖身契”,允许妓女从良。1951年春,王桂花离开妓院,经居委会牵线,嫁给了一个名叫宫平道的男子。
宫平道的老爸是英商电话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兼股东,可想而知是一个知识分子,娶的妻子也是知识分子,在法租界广慈医院从事化验工作。两人成婚后,生了三个子女,两女一男。两个女儿大学毕业后嫁给了洋人,小儿子宫平道却让父母头痛。
这位富家公子的长相没得说,集中了父母的优点,一米七五的身高,不胖不瘦的身材,相貌看着也顺眼。如果评选美男子,遇到类似屠世臻那样的对手,当然是要落选的,但拿个提名奖应该没有悬念。遗憾的是,宫公子的脑子似乎有问题,坊间老百姓的说法就是“脑子里少一根筋”。
单单少一根筋倒还好,这个宫平道还有“花痴”倾向。每当春天来临,郊野四下里油菜花盛放,春色盎然花香扑鼻时,四邻八舍就该提防宫家那个“阿三头”了,不但少女少妇要严加提防,即便中年妇女也不敢大意,唯恐遭受“阿三头”的骚扰。也有防不胜防的时候,那宫家就只有花钱来摆平了。
这样到了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了,对宫家的态度就强硬起来。派出所民警登门警示,跟宫平道本人当然是说不通的,白费口舌,就把责任压到父母头上。父母商量下来,没奈何,还是掏钱吧。不过,现在是新社会了,过去那一套出事后花钱弥补的老办法行不通了,这钱钞得用在未雨绸缪方面,每年4、5两个月,雇两个身强力壮的闲汉到家里来日夜看着儿子。
这样做也只是权宜之计。宫公子脑子有毛病,身体可壮实着呢,平时感冒发烧都少见,估计寿命长着哩!一劳永逸的法子倒是也有,那就是替他娶个媳妇。可宫平道的名声不佳,父母托人物色了好几个对象,人家都不干。此时新中国的婚姻法已经颁布实施,不能像旧社会那样掏钱买个媳妇进门了。老宫夫妇正头痛的当儿,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来说媒了。她们受上级指派,要求动员起来,为从良妓女解决择偶问题。
老宫夫妇在政治方面比较敏锐,对解放以来新政权的治国路数已经明了,知道凡事都应响应政府号召,不能有顶风逆流之心,更不能挑三拣四,干脆给儿子物色一个“受苦姐妹”(当时社会上对妓女的称谓)进门算了。
就这样,王桂花成了宫家的儿媳妇。她也识相,知道新社会新风气,旧时彩礼那一套就免了,但结婚不能没房子。她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宫家必须提供一套产权属于宫平道和王桂花共有的独门独户的房子作为两人的新居。
这个要求对于宫家来说不算苛刻,老宫夫妇把一如里之前出租的上下六间带天井的一座小楼给他们作为婚房,配置了全新的家具和生活用品,还给了两人一千二百万现钞。以1951年的物价,这绝对是大手笔。二人成婚那天,王桂花乘坐宫家从“强生出租车公司”租来的婚车前往一如里,在民政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过门,成为坊间的一个重大新闻,不仅一如里,甚至长宁路部分路段都是观者如云。王桂花由此在这一带出了名。
宫平道娶了王桂花之后,“花痴”症状果然到此为止。不过,智商依旧。父母听说中医或许有法子对付,就访到了一个老中医,老中医建议除了吃药,还可以通过气功、太极拳、钓鱼等活动静心养性。老宫夫妇认为钓鱼可以一试,遂给儿子买了钓具。没想到的是,儿子竟然从此喜欢上了钓鱼,还交了几个钓友,每次出去垂钓还都有收获。
三个月前,宫平道与钓友去浦东唐家湾钓鱼时突遭暴雨,几人躲进河边一个牛车棚。雨停后,鱼儿浮游水面,正是钓鱼的好机会。几个钓友纷纷行动,宫平道那边很快就有鱼儿上钩。这条鱼还不小,被宫平道用钓竿拽到岸边,正待俯身去捉,脚下一滑,身子没稳住,一头栽到河里。这条河不算宽,但很深,正是涨潮,水流湍急。宫平道不会游泳,众人眼睁睁地看着他冒了三次头,就再也没能浮上来。
现在,王桂花被专案组盯上了。组长卢禄定带着三名侦查员来到派出所了解王桂花的基本情况,上述她跟国民党特务之间的瓜葛,是后来才知道的。
侦查员认为,王桂花目前独居,且其居所位置处于一如里这条“死弄堂”(沪上坊间把只有一个出入口的弄堂称为“死弄堂”或者“断头弄”)的最后一家,打开后门就是另一条马路,这种条件,容易被屠世臻这样的资深特务作为栖身处。长宁路派出所的林所长遂派户籍警前往一如里,悄然把居委会主任和治保委员请来,了解王桂花最近的活动情况,以及家里是否有外人出入。
两个居委会干部都说,近日没见王桂花家里有陌生人出入。不过,这并不能排除她在家中留宿外人的可能性。王家后门那条小马路有数十米长,两侧都是工厂或仓库的围墙,既无商铺也无住家,倘若从后门出入,恐怕不会有人留意到。那么,该如何弄清楚其家中的情况呢?待居委会干部离开,老卢对三个侦查员凌亚敏、丁金刚、裴云飞说:“你们都有什么想法?”
几人你一言我一语正商量着,林所长带着那二位居委会干部之一刘阿姨去而复归。老卢立刻意识到有新情况了。
果然,那位刘阿姨说,刚才和居委会主任出了派出所,两人分别走了两个方向回家。刘阿姨穿过马路,正好遇见从菜场买菜出来的居民章婶。她心里一动:章婶就住在王桂花家对面,不知她是否看到过什么情况。
遂驻步招呼对方,先扯了几句闲话,临时编造的说法是有人托她问问王桂花是否有意再嫁。章婶说:“我看她是打算再嫁的,不止是打算,没准儿已经有对象了。”
刘阿姨忙问何故。章婶说,最近一段时间她在夜深人静时起来给豆芽浇水(章家男主人是经营绿豆芽、黄豆芽的小贩,发豆芽过程中,晚上要定时浇水),经常听见王桂花家里有动静,有时还传出很轻的男子说话声。就在刚才,章婶出门买菜,还听见王桂花在里面说话,说的什么没在意,好像称对方“李先生”。刘阿姨寻思这个情况得赶紧报告派出所,遂转身回来了。
卢禄定听到“李先生”三字,立刻想起那个姓葛的三轮车夫提到过,酒醉加药性发作的袁维珍以“倪先生”称呼屠世臻,沪语中“李”、“倪”二字发音相近,王桂花所称的“李先生”,多半就是“倪先生”!当下二话不说,抬手按了按怀里的手枪:“那就立刻行动!林所长,你这边能否找几个人手,最好是有实战经验的,带上武器,帮我们守住弄堂口?”
“没问题!”
四名侦查员随即离开派出所,直扑一如里王桂花的家。到得门前,也不叩门,精谙格斗的彪形大汉丁金刚二话不说一脚踹开。侦查员穿过天井,冲进客堂。定睛一看,八仙桌一侧坐着一个正在斟酒的男子恰好王桂花端着热气腾腾的砂锅从厨房出来,见状一个激灵,砂锅落地,四分五裂,沸汤乱淌。
该男子正是屠世臻,他是老特务,估计以前也曾遇到过此类情况,当下一跃而起,身形移动之间,手里已经握了一支手枪。可他还没来得及瞄准,已被旋风般冲到跟前的丁金刚一掌劈在手腕上。手枪顿时被砸飞,屠世臻惨叫一声,左手捂住右手手腕,疼得脸色煞白,事后才知道,老丁这一掌竟然将其腕骨劈了个骨折!
十一、“刺猬方案”
屠世臻、王桂花落网后,随即被押解市局。卢禄定主持了对屠世臻的讯问,获得以下情况。
抗战胜利后,屠世臻被派赴海外从事情报活动,1950年因贪污特费事发,调回台北关押数月后降级使用。1951年得以重新启用,派至“保密局”香港站任外勤组长。也许是流年不利,在抓捕一名越南“工作对象”时,不知怎么地认错了目标。更糟糕的是,那个被认错的对象拒捕,在打斗中挨了一枪,送医院抢救不及,一命呜呼。很快弄清楚,死者竟然是香港警队的一名便衣!紧接着,他这个小组连他在内的五名特务被香港警方逮捕。

这次事故动静很大,港方把五名特务送上法庭,审理下来,为首的屠世臻获刑七个月,这已经是考虑到台湾方面的面子了。
1952年3月,屠世臻刑满释放返回台北。一下飞机就被等待在机场的“保密局”特务带走,按照规矩又是一通审查,折腾了三个月,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念其系“军统”时期的资深同志,且已在香港蹲了七个月监狱,不再给予降级处分,但记过一次,存入档案。
屠世臻被搞得灰头土脸,寻思留在台北估计没有翻身之日,遂要求再去香港站,“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好歹也要立下功勋,挣回面子。上峰答应可以考虑。他想想不稳当,又备了一份重礼,送给人事处长。
这下算是定心了,等了个把月,人事处的通知下来了,命其以“保密局”联络副官的身份潜赴上海,执行一项名谓“刺猬方案”的绝密任务。屠世臻本想去香港,结果却被派往上海,虽是百般不愿意,也无可奈何了,只能在心里把人事处长一家骂了个遍。
其时朝鲜战争打得正酣,台湾方面一直想利用“韩战”对大陆做些动作,什么“反攻”、“光复”之类纯属做梦,但趁机多发展一些特务,建立若干秘密潜伏组织之类的“小目标”还是可行的。于是,“保密局”派人前往上海进行特务活动。
当年“军统”在上海组建了“军统”上海区,其下辖的上海站、苏州站、杭州站,除了有编制的正式特工,还有若干类似临时工或钟点工的编外成员,比如前面说过的“一枝花”袁维珍、“一掘头”尹关先就是这类角色。编外成员中不乏江湖成名人物、身怀绝技的黑道高手,也有身居重要岗位者,比如电话局技工、铁路局调度员、银行金库保安等,他们是由在编特工一对一发展的,其中有些曾协助“军统”执行过一些特殊任务,有的则尚未动用过,处于隐身状态,等候着“组织”的召唤,直到上海解放也没参与过任何特务活动。
此次“保密局”制订的“刺猬方案”,就是要从原“军统”人事密档中调出这些人的材料,从中遴选若干人作为首批激活或发展对象。之所以将屠世臻派遣上海执行这项任务,是因为屠世臻在抗战期间一直在沪上活动,熟悉环境,还跟部分“暗棋”或准“暗棋”打过交道,甚至指挥他们从事特务活动,比如袁维珍、尹关先和王桂花。
袁维珍和尹关先是江湖黑道上的成名角色,名列首批发展对象之中。至于王桂花,原本是入不了具体制订“刺猬方案”的“保密局”特工专家的法眼的,屠世臻了解到任务的具体内容后,认为王桂花的住所可以作为自己的安全栖身处,遂向上峰提出,将王桂花纳人名单。“保密局”通过上海的潜伏特务组织对王桂花进行了一番秘密考察,方才批准了屠世臻的请求。
考虑到屠世臻潜入沪上后可能会遭遇的“万一”,“保密局”对方案的细节进行了精心策划,比如被列入首批名单的十七名成员,除了王桂花、袁维珍、尹关先等屠世臻原先就打过交道的,其他成员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屠世臻在出发前并不知情。待其安全抵沪,再通过事先约定的方式在指定的地点与其进行交接。至此,屠世臻才拿到了那份完整的名单,当然,是使用密写药水书写的。屠世臻把名单上的内容默记于心(这是作为一个特工必备的素质),随即销毁。
根据计划,屠世臻与这十七名成员面对面拍板敲定后,要起草一份密电放在约定地点,由其他潜伏特务组织拍发台北。而拍发这份密电所需的密码本,就藏在那个“百雀羚”盒子里。
至此,我们终于知道那个神秘的“百雀羚”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了,那是一份关系到“刺猬方案”最终成败的生死符。屠世臻抵达上海后,先是在王桂花的住所栖身,就把这份“生死符”藏匿于王家的某个隐蔽角落,女主人并不知晓。稍后,他又跟袁维珍接上头,发现这个“清倌人”竟然对自己感情依旧。
如果让屠世臻在十七名成员中选出一个他最信任的人,他无疑会把票投给袁维珍。那个“百雀羚”盒子,自然也就从王桂花家转移到袁维珍的住所。他把盒子直接交到情人手里,千叮万嘱:“这盒子里放着回头我们一起去海外的‘钥匙’,务必藏好!”
袁维珍的住所位于冷僻的甜爱路,屠世臻认为这里的安全系数要比王桂花那里高。应该说,这个判断没啥问题。但袁维珍得变化,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怎么说呢?那个年代有个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说法:“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袁维珍的变化就是真实写照。这个江洋大盗出身的青楼女子,尽管抗战期间做过“军统”的临时工,但其实她对政治从来不曾关心过;解放前是这样,解放后也是如此。可是,中共领导下的新社会就是有那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神奇魔力,袁维珍不关心政治,政治却来关心她了。
其时上海已经解放三年多,无处不在的新气象新思想,就像一阵阵无孔不入的清风,润物无声地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个人。袁维珍对于周围的变化也不是完全无感,但并未与自己联系起来。当她决定跟随梦中情人潜赴海外去过她向往已久的幸福生活时,忽然对解放后身边发生的一切产生了强烈的留恋之情。这种情感就像打开了一道闸门,三年多来从没有刻意去记忆的新社会的一幕幕浮现眼前。历经三天三夜的反复思虑,她作出了决定:不去海外了!不但自己不去,还要劝屠世臻也留下。他是特务不假,可政府有家喻户晓的坦白从宽政策,我要动员他向政府自首,坦白检举,立功赎罪!
袁维珍是江洋大盗出身,对黑道规矩了如指掌,对于特务这一行的思维模式却完全摸不着边。当晚,她就把自己的心思向屠世臻和盘托出。可以想象,屠世臻闻听此言时该是何等震惊。缓过神来,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将袁维珍灭口,但马上强迫自己按下了刹车键:不能啊!“生死符”还在她手里,不知她藏在哪个旮旯!如果现在就向她索要,肯定会引起怀疑,得先哄着她把“百雀羚”盒子交出来再灭口。屠世臻故意沉吟半晌,才提出让他考虑两天。
这天是10月16 日。次日上午,屠世臻仍然像往常那样外出,联系名单上的其他成员。袁维珍不知道他究竟去干些什么,也不多问。
屠世臻既然已经动了杀机,就开始考虑怎样不留痕迹地结束袁维珍的性命。他以前参与过一些暗杀行动,对杀人并不陌生,但仓促之间要他不留痕迹地处理掉一个大活人,手头又没有相应的药物或器械方面的准备,还真是有点儿犯愁。这天他跟两个名单上的成员见面,下午见第二个成员老苗时,终于在脑子里生成了一个主意。
老苗并不姓苗,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他是苗族人。老苗于1935年来到上海,在南市老城隍庙摆地摊卖草药。他有一门祖传独家本领,擅长配制各种各样的毒药,在云贵川一带是个颇有名气的“毒药专家”。如此,就难免跟江湖黑道扯上关系,被官府盯上,不得已才逃到上海以卖药为生。当然不敢给别人有偿配制毒药了,老老实实卖草药。
抗战爆发后,信息灵通的“军统”特工闻知老城隍庙还藏着这么一个特殊人才,就打算把他发展为外围成员。也不知“军统”是怎么做他思想工作的,反正老苗答应必要时可提供协助。待抗战胜利,“军统”搞复员,像老苗这样的自然无人搭理,遂与“军统”中断了关系。
现在,屠世臻又找上了他。据“保密局”在沪上的潜伏小组调查,解放后老苗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不仅是他“毒药专家”的身份,而且公家人认为他历史不清,为此,还把他收容审查了三个月。最近又有新动向,云贵川方面频频有公家人来沪找他外调,老苗焦头烂额,担心政府翻旧账,那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因此,听屠世臻说明来意,老苗马上表示愿意随其一起去台北,为“保密局”效力。
谈完了正事,屠世臻把话题转到对方的专业上,“随口”聊起如何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要人的命,还查不出真正的死因。老苗已把屠世臻作为上司看待,有问必答,当下呵呵一笑:“这还不是小菜一碟?”说着,拿了个纸袋装了些覃菇干递给屠世臻,告诉他只消如此这般就解决问题了。
当晚,屠世臻宿于甜爱路。袁维珍见他并未像断线风筝一般一去不返,更是相信他没有欺骗自己。屠世臻正盘算怎样套问那个“百雀羚”盒子藏于何处,袁维珍主动开腔了,问那个盒子里有什么秘密。屠世臻如实相告,但这只是个铺垫,往下才是重点:“既然你不打算跟我去台湾,我一个人去也没什么意思,这个盒子里的东西也就没用了。不过,你还是要收藏好,如果我决定去自首,那是要交给政府干部的。”
袁维珍听屠世臻话里话外透露出愿意自首的倾向,高兴还来不及,哪里还作他想?随即拿出钥匙打开床头柜:“我把它藏在这里了。”
看到“百雀灵”盒子,屠世臻终于放心。晚餐时,屠世臻就想拿出覃菇干煮汤,又担心袁维珍毒性发作癫狂起来惊动邻居,到时自己不好脱身,就没有行动。
10月18日,屠世臻出门较早,临行前提议中午碰头,两人一起去“小四川”吃饭。就这样,毫无提防的袁维珍着了屠世臻的道。
接下来,就是取回那个“百雀羚”盒子了。屠世臻生怕警方对袁维珍之死生疑,不敢自己去,遂想到了“一掘头”尹关先。反正尹关先是他下一个要接触的对象,干脆让他把这事办了吧。哪知尹关先去搜查了一遍,却没发现那个“百雀羚”盒子的踪影。
不得已,屠世臻只有自己出马了。第二天晚上,他冒险前往甜爱路。刚到袁维珍住处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锤子敲击的声音--其时裴云飞正在用斧头砸客厅的地砖。他意识到可能穿帮了,当即转身离开,不敢再动去袁宅搜寻那个盒子的念头。
此后,屠世臻又回到长宁路一如里王桂花家避风头。名单上的十七名成员,他已经联系上了十五人(包括已经死去的袁维珍),剩下两个缓一缓也不妨事。既然密码丢失,暂时跟台北联系不上,只有等台北方面派遣潜伏特务联系自己了一册上峰知道他藏身王桂花家,自己这边长时间没动静,自是要设法弄清楚发生了什么状况。
讯问结束,卢禄定向上海市公安局扬帆局长汇报了一应情况。扬帆局长当即下令,出动上百军警,分头将名单上的十四名成员抓捕归案其中袁维珍已死,尹关先、王桂花已落网,还有两个屠世臻没来得及联系的,警方帮他“联系”上了。
但这个案子破得还不算圆满,因为尚未找到那个“百雀羚”盒子。当天下半夜,专案组全体出动,还请来了市局技术人员,对甜爱路36号甲进行了一番彻底搜查,就差把房子给拆了,依然没发现那个盒子的踪迹。
裴云飞想到了一种可能性--袁维珍对情郎抱有很大期待,会不会打算吃饭时继续劝说屠世臻自首,来个速战速决,饭后就陪着屠一起自首,因而干脆把“百雀羚”盒子带在身上了?而屠世臻压根儿没想到这一层,两人坐三轮车返回时,他窃取了袁维珍的家门钥匙,却没留意那个盒子也在袁的身上。结果袁维珍毒性发作,被汽车撞飞,那个盒子从身上掉落,比如,滚到附近的下水道里去了?
专案组根据这个思路,终于在甜爱路与四川北路交界处的一处窨井里找到了那个“百雀羚”盒子。
1953年1月中旬,屠世臻、尹关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王桂花、阮顺七(老苗)等案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不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