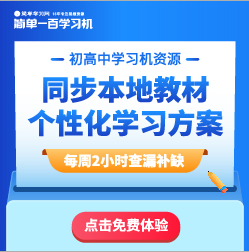七、虚荣的谎言
4月23日午后,“103专班”第六组三名侦查员裴云飞、张伯仁、丁金刚抵达镇江,直接去江苏省卫生学校旁边的四牌楼旧货市场。
此时距廉梦妍淘得那对玉杯已有六年,由于政府加强了对收旧、典当行业的管控,并开始试点公私合营,四牌楼旧货市场的买卖已经不像当年那样红火了。市工商局在该市场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税务局也派来了一个常驻市场的税管员,一句话----管理纳入正轨了。这一纳入正轨,就把摆地摊的小摊贩给惊走了。侦查员在市场里转了一圈,也没看到廉梦妍所说的那类出售瓷器的小贩,只有几家小店在卖宜兴茶具以及估计是从关门歇业的饭馆经营者那里收得的碗盆碟勺之类的瓷器,向店主打听卖旧瓷器的小老头儿,都摇头说不知道。
那就只有去问问工商局的工作人员了。工商局在旧货市场的办公室有三个办事员,被称为“柳主任”的那位是一个气质老成的中年人,看过侦查员出示的证件和公函,他热情招呼三位落座。侦查员开门见山道明来意,柳主任说这边市场里原先地摊甚多,最近半年日趋减少,大约走掉了五分之四,剩下的五分之一,也没有卖瓷器的。说着,他转脸问两个属下之中那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小金,你比我们早进市场,看见过那么一个卖瓷器小件儿的小老头儿吗?”
当初镇江市人民政府决定往旧货市场派驻工商税务,先让工商局的工作人员打前站,每天像寻常群众那样来逛市场,了解市场的经营状况,为了装得像,有时还买点儿小商品,小金就是专门干这差使的。这姑娘记性很好,观察事物也比较细致,当下想了想说:“印象里是有那么一个小老头儿,在市场西门内那棵银杏树下设摊卖瓷器小物件,我还给侄子买过一个能够吹出鸡鸣声响的瓷公鸡哩,小侄子现在每天早上还要吹一阵,惹得邻里的公鸡都此起彼伏地跟着打鸣。哦,对了,根据领导的指示,我还跟他聊过几句,了解小商贩对政府的管理有什么看法……”侦查员一听似乎有戏,忙问:“有没有问这个小老头儿姓甚名谁,家住哪里?”
“问倒是问了,可时间太久,已经记不得了。”见侦查员脸上露出失望之色,小金马上补充,“不过,当时我跟每个小贩的谈话内容,都记在工作手册上了。”
说着,小金打开写字台一侧的柜子一通翻找,果然找出了三本工作手册,很快查到记录着跟那小老头儿聊天内容的一页。裴云飞接过一看,上面有小老头儿的名址:沈鹏顺,朱方路三德里 19号。
三位侦查员直奔朱方路派出所,一提沈鹏顺,派出所民警说管段里的确有这个人,不过现在已经不归他们派出所管了。侦查员不解:“这是什么意思?他搬家了?”
民警说:“这老头儿是租居户,在这边住了五六年了,户口是1948年由旧警署给上的,解放后我们按照规定沿袭登记。半个多月前……嗯,应该是4月2日吧,市局政保部门来了辆小吉普,把他给带走了。
“因为啥事儿?”
“听说那老小子在老家做过土匪,反动派闹还乡团时他也参加了,利用走街串巷做旧货买卖之便给人家打探消息。解放后他就逃到镇江这边躲起来了。最近市局政保部门收到检举信,就把他抓了,关押在市局看守所。按说这种对象是要被押回老家审判的,现在他是不是还关在看守所,那就不清楚了。”
裴云飞和张伯仁商量片刻,决定直接去看守所打听,如果没押走,那就立即讯问;如果已经押回老家了,就把与其同一监房的在押人犯开出来,了解沈鹏顺在关押期间是否聊起过有关那对玉杯的情况,同时跟沈鹏顺原籍的公安机关联系,做好去沈的原籍地了解情况的准备,只是这-番折腾,难免要耽误些时间。
三人的运气还不错,沈鹏顺尚未被押解回原籍,看守所方面已经二次去函沈鹏顺原籍地公安机关,催促他们派人过来把该人犯提走,估计这几天也应该来人了。
很快,看守民警将沈鹏顺从监房开出来。这小老头儿一看来了三个便衣,眨着一双耗子眼,眼珠子滴溜溜乱转,似在猜测对方的来路。侦查员也不跟他啰唆,由旧警出身惯于装腔作势的张伯仁开口说明外调来意。沈鹏顺听着,露出不解的神色:“你们是上海的?我今生从没踏进过上海滩一步,哪里知道上海的什么事情?”
“你虽然没去过上海,但跟来镇江的上海人打过交道嘛。”张伯仁遂提起1947年夏天沈在四牌楼旧货市场摆摊期间跟卫校女生廉梦妍的那桩买卖,临末问,“还记得这事吗?”
沈鹏顺连连点头:“记得记得!”
裴云飞听对方回答得这么爽快,心里便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这主儿是以出售旧瓷器为业的,经手的大大小小瓷器不计其数,而廉梦妍在旧货市场淘得那对杯子是六年前的事,这小老头儿怎么记得那么清楚,此刻一问就想起来了?当然,这只是裴云飞脑海中的一闪念,此刻还不宜提出质疑,且听他怎么说吧。
张伯仁继续问:“你卖给那个姑娘的那对杯子是从哪里弄来的?”
沈鹏顺的回答跟雷理娟所说并无差别,即从郊区----镇江东门外七里桥镇梢头的一户黑门牌老太太家收购来的,两个杯子的收购价是一块银洋,他卖给那个卫校女生是两块银洋,这笔买卖做得合算,他从苏北逃到镇江这几年以来,这样的买卖难得遇上几回,所以印象深刻。
侦查员感觉沈鹏顺不像在说谎,又问了问那个黑门牌老太太的情况,但时隔太久,沈鹏顺只是对那个黑门牌有印象,其他的就说不出什么了。
离开看守所,侦查员直奔七里桥。七里桥的确有一座古石桥,镇子就以这座石桥命名。七里桥镇不大,就是东西一条街,大约有一华里长。三人转悠了一个来回,却没见有哪户居民门上钉着黑门牌的。张伯仁心里不踏实了,嘀咕说:“别是给那家伙耍了?”
丁金刚说:“咱们还是去派出所打听一下吧,既然是门牌,应该归派出所管,钉上或者取下都是户籍警的事儿嘛!”
裴云飞、张伯仁认为言之有理,就向街边住户打听派出所的位置。可是,这个镇子过于袖珍,没有设派出所。那就只好去镇政府打听了。镇政府驻地也有点儿寒碜,设在一座名唤“将军庙”的废弃庙宇里,简直可以算“危建了,连同镇长在内,一共只有四名干部。分管治安工作的是一个姓岳的中年男子,身份既是镇政府干部,又是民兵连长,管着镇子周边五个村庄的民兵。侦查员跟此人甫一接触,顿感“凡人不可貌相”,这个干部看外表跟城郊农民无甚区别,来头却不小--
他是抗战前期新四军驻茅山部队的一名侦察员,被派到镇江潜伏,从事情报工作。后来地下交通线遭到敌人破坏,他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老岳是走江湖打拳卖药出身,有些功夫,当晚便打死岗哨越狱,躲到七里桥的将军庙出家为僧。性命是保住了,也算有了一份职业,至少饿不死,但跟组织上的联系也中断了。如此一直到镇江解放,方才去市委组织部设在镇江市内的“失散同志报到处”进行登记,顺利通过组织上的审查,回归革命队伍。可是,党员身份作废了,必须重新申请入党,而且党龄要从获准重新入党之时起算。因此,老岳虽是1938年的老新四军,但党龄还不到两年。
老岳对镇上的情况很熟悉,听上海来人如此这般道明来意,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有这么个老太太,姓安,还住在七里桥镇上,我带你们过去。”
路上,老岳告诉侦查员,这个安老太出身富家,其父据说是清朝军队的下级军官,离开行伍后回到镇江老家开了一家织布厂,又在轮船公司人股,还盘下了一家古玩店。其父有一个绿林出身的严姓江湖朋友,金盆洗手后在七里桥置地造屋。两家多年前定下了娃娃亲,安老太成年后就嫁给了严家的独子严茂仁。两人成亲不久,严茂仁的老爸去世,家产遂传到他的手里。
严茂仁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因患病未曾就业,一直在家写字画画,修身养性。继承了家产的严茂仁并无“发扬光大”之想,全家日常生活靠收地租和放债的利息。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受“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对租地户债务人比较宽容,从来不逼债,地租债务收不回来,就变卖田产补贴自家开支,当地坊间称他为“慈仁公”。
至于黑门牌,则是因为他留学日本的那段经历。抗战爆发前,他跟曾经的日本同窗过从甚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镇公所认为严家有“通敌嫌疑”,就给钉上了黑门牌。解放后,人民政府否定了伪政府(初解放时社会上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称谓)的做法,把黑门牌给摘了。不过,大前年土地改革运动时,严家被定为工商地主,没收了地产、投资股份和家中的部分财物,原先的佃户还给严家的门框上钉了一块“地主”木牌
说话间,老岳在镇梢头一户民宅前驻步,说“到了”。三侦查员见门框上的门牌与镇上其他住家一样,也是蓝底白字,旁边并无“地主’木牌,不禁觉得奇怪,均朝老岳投以不解的目光。老岳对此作了一番说明--
今年3月下旬,镇政府收到武汉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发来的一份正式公函,大意是他们最近在整理从部队转过来的“未找到家属的革命烈士”材料时,发现一位名叫严仕琰的烈士的家庭住址是江苏镇江七里桥,便将该烈士的简况寄来,希望协助调查该烈士的家属是否在七里桥镇上。
严仕琰烈士于1940年参加革命,同年人党系中共武汉市委地下情报人员。抗战胜利后,调至中共湖北省委情报部门担任组长。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华中局社会部根据中央命令向军方调派若干名情报人员,严仕琰奉命调至军方,其关系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政治部下辖的情报处,担任军方在武汉市的一个潜伏情报组的组长。武汉解放前夕,该情报组暴露,严仕琰在掩护同志撤离时,与国民党军警枪战,在击毙两人后中弹负伤,果断饮弹自尽,壮烈牺牲。
老岳在七里桥镇已经待了数年,对全镇住户的情况了如指掌。镇长看过武汉方面的公函,问他镇上有几户姓严的人家。老岳告诉镇长,全镇就一户姓严的,就是严茂仁家。他确实有个儿子,名字不清楚,抗战爆发那年报考国立武汉大学被录取,离开镇江前往武汉上学后就没了消息。不久南京沦陷,交通几乎隔绝,严家屡屡向武汉大学、武汉市警局、湖北省警察厅发函电查询,均没有回应。武汉沦陷后,严茂仁曾赴武汉寻找儿子,找了两个月没找到,只得快快而返。严家人还特地跑到南京和上海登报寻找儿子的下落,甚至斥金请两地著名命相师推算,都说“已殁于战火”。严茂仁终于断了念想,在七里桥镇外邢家湾祖坟为儿子建了一座空坟,至今还在。
镇长和老岳随即去了严家,先不提公函,而是拿出随公函寄来的一张严仕琰生前笔迹的照片请严茂仁辨认----这是武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从武汉大学保存的学生档案中找到的。得到确认后,方才告知情况。搞情报出身的老岳心细,起草公函回复武汉方面之后,又向镇江市政府汇报了这个情况。市领导颇为重视,责成市民政局关注此事。
武汉方面收到回复公函,派人将烈士证书专程送到七里桥。按照当时的政策,有了这个烈士儿子,严茂仁虽然还是地主成分,但已不再属于“专政对象”,而是被归入了“进步士绅”的行列。而且,镇江市民政局还向上级主管机构江苏省民政厅上报了革命烈属材料。日前传来消息说,下周市民政局将派员来镇上,为老严家挂“革命烈属”的光荣牌,原先那块“地主”木牌,自然就摘下来了。
原来如此,侦查员放心了,既然是革命烈属,那就不必担心人家不配合调查了。可是,进了严家坐定之后方才知晓,那位革命烈士的母亲安老太不在家,上周她去广州探望女儿严仕琴去了。严氏老两口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严仕琴是严仕琰的妹妹,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嫁了一个华侨名医,1948年定居广州。严氏老两口本打算去广州探望的,但那时国共内战正酣,难以成行。好不容易解放了,家里又被挂上了“地主”牌子,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只好自认倒霉。现在“地主”牌子摘了,安老太思念女儿,不顾老伴反对,孤身赴粤看望爱女。
侦查员听说这个情况,不由得面面相觑,安老太不在,往下该怎么调查?
严老爷子见状开腔了:“老朽斗胆问一句三位公安同志,此番来找拙荆,不知所为何事?”裴云飞遂简述了来意,问严老爷子知不知道安老太处理旧瓷器之事。
严老爷子点头:“这事我知道,那个小老头儿来镇上收购旧货时,我去镇江城里找朋友挪头寸去了。不瞒三位说,解放后本户经过土改抄家,其实也没受多少损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在解放前,我这点儿家底就已经被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差不多榨干净了,全家的生活仅靠小儿子在轮船公司的薪水以及女儿的贴补。本已捉襟见肘,偏偏又赶上孙儿患病,无钱医治,老朽万般无奈,只好进城去找老友挪头寸。待借得一笔钱回来,儿媳妇却已经带着孩子去镇江城里看病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拙荆把家里的古杯卖掉了两个……”
侦查员听老爷子说“卖掉了两个”,脑子里顿时产生联想--看来他家的古杯不止两个。一问,果然,老爷子说:“这种东西,我家有一缸哩!”
裴云飞瞬间有一种懵了的感觉,怎么着,这等稀罕的南宋皇室玉杯有一缸,还需要借钱给孙子治病?随便出手两个不就得了?张伯仁倒是马上明白了:“老先生,您说的这'古杯’莫非是仿制品?”
严茂仁笑了:“若不是假货,土改抄家时哪会给老朽留下呢?”
说罢,他起身引领侦查员去了后院堆放杂物的披屋,屋里有一个被乡间称为“七石缸”的陶瓷大缸,里面放着大半缸瓷器,除了杯子,还有碗碟、大小勺子以及笔洗、笔架、镇纸等文房用品,虽是仿品,倒也算制作精细,一件件温润如玉。
那么,这些瓷器有什么来历,严老爷子为何攒了这么些?
严老爷子告诉侦查员,当年他从日本留学回国,有一个名叫兵部三郎的日本同窗同行。这主儿是个出身门阀的纨绔子弟,读书成绩可想而知,但人品还可以,喜好交友,遇事仗义,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像当时日本社会上大多数青年那样满脑子军国主义。他在学校里结交了几位中国留学生朋友,严茂仁也在其中,而且被他认为是“最值得交往的异国友人”。严茂仁完成学业准备回国,兵部三郎宁愿放弃补考(他的成绩太差,那年没考过),缓一年再冲文凭(也就是留级),也要兑现之前与“严桑”的约定----由严茂仁陪着去中国江南地区看看。
兵部三郎跟着“严桑”来到镇江,先是在镇江本地转悠,然后去南京,再就是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杭州、鹰潭,最后到了景德镇。这时,严茂仁接到家里的急电:老母病重速归!
这就必须立马动身返乡了。以兵部三郎的性格,他本当随行的,不巧正赶上他水土不服上吐下泻,无法上路,那就只好先留在景德镇了。这东洋少爷倒是很讲究礼仪的,当即开了一纸五十银洋的支票,硬塞给严茂仁。
严茂仁急急赶到家中,其时老母经家人跑到南京请来的名医诊治,已转危为安。严茂仁遂往景德镇发了一封电报告知情况,并询问对方的病况。兵部三郎回电说,他已基本痊愈,本想立刻赴镇江的,现在得知伯母无恙,那就继续在景德镇盘桓数日,景德镇乃是举世闻名的瓷都,他得好好转转。还叮嘱严茂仁在家里多陪陪母亲,等他游览完景德镇,就去镇江看望伯母。
过了七八天,严茂仁接到兵部三郎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说他有要事须立刻回国,此刻已抵沪,即将登轮,不及面别,有失礼仪,万望见谅。另有一事拜托,他在景德镇参观一处废窑时,斥资从窑主那里购下其数年前烧制的一批仿古瓷器,因景德镇无法办理海关手续不能直接托运回日本,故先托运至镇江七里桥镇严宅,烦请“严桑”代收。他回国处理好家事后将再度赴华,届时办理手续,将这批瓷器托运回国。
半个多月后,果然有五大箱瓷器运至镇江,严茂仁收到货运单,即去镇江火车站提货,同时致电东京告知兵部三郎,却未见回音。后来又发了几次电报,依旧联系不上。严茂仁遂买了一口大缸,将五个木箱里的瓷器放入缸内保存。
他曾给毕业后定居日本的中国同学写信打听兵部三郎的下落,人家要么没回信,要么就是复函说“不清楚”。待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成为敌国,他生怕惹上“汉奸”嫌疑,不敢再给日本那边去信了。抗战胜利后,大批日侨被遣返回国,严茂仁也曾托其中的熟人回国后帮忙打听兵部三郎的下落,还是杳无音信。就这样这一缸瓷器一直放到如今,已有三十余年。
土改期间农会来人抄家,大家都知道他以往对佃户、债务人比较宽厚,从来没有穷凶极恶催逼地租或债务之举,甚至因此不得不卖田典地贴补家用,料想他不会私藏浮财,抄家时对他就比较客气。这一缸瓷器本不值什么钱,严茂仁也没藏着,大大方方给农会的工作人员看了,人家一件件拿出来检查,又一件件放回去,说这也算不上剥削所得,就不必充公了。只是经过这一番拿出来放回去的折腾,难免弄碎几件。严茂仁在后院挖了个坑,把那些碎片都埋了。
裴云飞、张伯仁、丁金刚三人听了严茂仁如此这般一番陈述,又看了老爷子出示的当年那五箱瓷器的提货单,以及当场从后院地下挖出来的瓷器碎片,均认为严茂仁的说法可信。当然,这是重大案件调查,还得做一份笔录,并拍摄了那些瓷器的照片。另外,他们还出具了借条,向严家借了几件瓷器,以便进行下一步调查。
4月24日,三侦查员返回上海,下了火车没回市局,而是直奔徐汇区新乐路派出所,请所方派员把雷理娟传唤过来。之所以称为“传唤”,是因为专案组对雷氏之前的说辞产生了怀疑。
雷理娟曾告诉侦查员,她把女儿从镇江带回的那对玉杯拿到古玩店,请店方鉴别。现在看来,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古玩店方面肯定是看走了眼,或者出于某种目的,故意睁着眼说假话。但玉器和瓷器之间的区别太明显了,别说古玩店,寻常人也分辨得出来,古玩店不太可能这么明目张胆地指鹿为马。那就只有另一种可能----雷理娟在说谎。
至于她为什么说谎,那就需要调查清楚了如此,往下跟雷氏的接触,就不再是对受害人家属的走访,而应将其作为调查对象来对待。
要说这雷理娟,虽是一个寻常护士,但在察言观色方面还是有两下子的。户籍警前来传唤她就意识到情况不妙。到了派出所,跟侦查员一照面,马上认错,说自己说了谎,骗了三位民警,她其实根本没把那对杯子拿到古玩店请人家掌眼。
女儿从镇江旧货市场淘得的那对杯子,她凭着出身典当行家庭积累的些许古玩方面的粗浅知识,一眼就看出乃是仿古瓷器。不过,仿制的工艺相当考究,材料也属上乘,应是仿古瓷器中的精品。她见女儿兴致勃勃,不忍扫她的兴,同时也动着以后女儿出嫁时冒充古玩真品作为陪嫁的脑筋--一则可以省下一笔钱钞,二则还能博个名声,遂佯称这是一对“南宋玉杯”。
廉梦妍哪辨真假,母亲说是,那就是了。女儿生性低调内向,倒是能够守口如瓶。
雷氏就不同了,她作假的动机中原本就有挣面子的成分,于是杜撰了“亡夫留给女儿一对南宋玉杯作为陪嫁”的说法,在小范围内一传播,自有好事者张扬开去。
那么,会不会是这套“虚荣的谎言”让案犯信以为真,最终导致凶案发生呢?第六组侦查员一时难下定论……
八、金相专家
晚饭后,裴云飞开始琢磨,案件目前为止尚未见效,说明六组的侦查路数出了问题,还有什么线索没有想到?对,那把黑色匕首!
4月20日案发伊始,六组前往复兴中路同裕坊勘查现场,对这把凶刀只是拍照、记录,在案情分析时并未作为一条线索来考虑。主要原因是这起案件中受害人与其未婚夫的关系迅速进入侦查视线,并作为调查的重点;同时,又盯着那对“南宋玉杯”进行调查,黑色凶刀有什么特别的吗?侦查员可能都把它当做一把普通凶器,无意中被忽略了。
次日,4月25日一早,裴云飞和张伯仁,丁金刚在驻地碰头,又一次研究起了这把黑色刀具。
这把黑色凶刀,其长度、形状与寻常人们认知中的匕首无异。裴云飞端详良久:“我虽是金工出身,接触的金属材料比较多,但主要是跟锁具打交道,这样的刀具,我还真没见过。老张警龄最长,阅历丰富,你以前见过这样的刀具吗?”
其实张伯仁之前已经提供过对这把凶刀的看法,凶刀之所以呈黑色,是在制造过程中使用了特殊的材料和热处理方式,目的是增强硬度和韧性。但他以前接触的案件以盗窃为主,对各种作案凶器的了解少之甚少。丁金刚也只是认为黑色比较特殊,仅此而已。那就问问金属方面的专家吧。
张伯仁、丁金刚先去拜访了一位名叫苏望鑫的老者。
苏老头儿是世代铁匠出身,对于他来说世代了究竟几代已经没有概念了,起码朱元璋造反那个年代,他的祖上就已经在为军队打造兵器了,距今少说也有五六百年了。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从海外回国,首站抵达上海,受到沪上各界的热烈欢迎,商界名流在张园设宴,席间向孙中山奉上的四件礼品中有一把宝刀,就是由被誉为“江南刀王”的苏望鑫的老爸苏遥祥打造的。报道中有老苏家爷儿俩的姓名,当时还是小苏的苏望鑫作为老爸的助手参与了这把宝刀的打造。
苏望鑫住在南市大境阁,张、丁两人合骑一辆摩托车前往。
“苏老先生,我们是市局侦查员,想找你打听个事,是关于冶金技术方面的,你听说过有一种黑色匕首吗?”
![]()
看过张伯仁带来的照片后,苏望鑫点头:“听说过,但没见过。你们可以去问问虬江机器厂的老铁,他应该知道。”
“虬江机器厂”位于虬江桥畔,距提篮桥监狱不远。这家工厂在民国时期就是“国企”,抗战爆发后迁到重庆,后由重庆迁回上海,是老牌的军工企业。
老铁的大名叫铁长乐,广东佛山人氏。铁长乐早年去香港学金工(即钳工),后通过了外轮船长的面试,成为英国货轮“海洋之花号”上的一名机修工,十三年后,他返回广东,在广州开了一家机修作坊。
稍后民国政府组建“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铁长乐担任检修车间副主任。像铁长乐这样的高级技师,说是钳工,同时也精通车、创镗、焊、电以及热处理等多种技能,堪称“全能金工”。
铁长乐看了看黑色凶刀的照片,说:“这种匕首是外国货,我以前在英国的旧货市场见到过一次。我估摸国内应该没有哪个铁匠能打造这种刀具,倒不是技术,是材料难寻。所以材料和制作应该都是在国外进行的,我能提供的就这么多。”
裴云飞自个儿去了江南造船厂,出示证件,拜访了金相研究室首席专家邬政,这位冶金权威端详着裴云飞出示的黑色匕首,沉思半晌方才开口:“黑色刀具我倒是见过,不多。但这种黑色匕首真没见过,更没听说过。”一边说一边拿起桌上的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罕见!实在罕见!制作这种匕首的钢材非常特别,裴同志,想弄清这把匕首的来历只有一个办法----从匕首上取少量金属粉末做一个金相分析。”
裴云飞马上点头:“谢谢先生!那就拜托了。”
邬先生把裴云飞带到旁边的实验室,吩咐助手作好一应准备,他亲自指点操作,用记号笔在匕首的血槽上端点了一下,叫助手在这个位置用一毫米直径的钻头打一个孔,收集金属粉末进行分析。助手依言照办,起初用的是高碳钢钻头,竟然钻不下去,遂改用实验室存量很少的特制合金钢钻头。这种钻头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人控制的江南造船厂(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改名为“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实验室的材料库里发现的,系当时最高端的精钢。
黑色匕首遇到特种钢材制作的钻头,这才服软,被钻出了一个一毫米直径的浅孔,那些金属钻花和粉末竟然也是黑色的,也就是说,用来锻造匕首的钢材本身就是黑色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邬政同样吃惊:“这世上还真的有黑钢,我算是开了眼界啦!”
裴云飞请教:“先生,这黑钢是怎么炼出来的?”
邬政看完送检匕首样品的金相分析后,作了个简单解说:“用来制造这把匕首的钢材是一种稀有材料,其特性跟刚才使用的日本合金钢钻头相似,硬度稍弱,但韧性强,估计是进行了某种改造,可能是成分上的,也可能是工艺上的。制作钻头的合金钢是日本的绝密技术,严禁向外泄露,但改进后的这种黑色特种钢,也许管控没那么严,不知通过何种渠道流入民间。至于为什么用来打造匕首,那我就说不上来了,这已经超出了我的专业知识范围。”
一旁的助手提议:“要不请小田先生来看看?”
小田是谁?小?
小田先生今年四十挂零,战前就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在日本排名第三的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金相研析室担任副主任。1940年,他被军方征调来沪,主持“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即江南造船厂)的研究工作。他是单身汉,在上海娶了一位中日混血的女子为妻。待到抗战胜利,小田先生不是军人身份没被国民党当局遣返,继续留厂效力,但职务被一撸到底,薪水也连降七级。解放后,日本共产党致函上海市军管会,这才知道原来小田先生是早在大学时期就已参加日共的老党员,战时与共产国际的情报机构建立了关系,收集了大量日军方面的情报。于是,他被任命为金相所的第二副所长。
说到这里,小田先生到了。这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身材瘦长精悍,裴云飞看着,寻思他多半是能文能武之辈。在邬政接下来的介绍中,果然提到小田先生在空手道、剑道方面多有实践,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江南造船厂每年举办的运动会上都有搏击项目,他铁定是能拿到名次的。裴云飞感叹之余,也产生了学武的想法:人家一个冶金专家都有这等身手,看来我也得物色一个武术名师学些拳脚了,毕竟咱是警察,不会点儿“三脚猫”的功夫,遇到紧急情况难道还靠别人保护不成?
小田听邬政介绍了情况,拿过桌上那把黑色匕首翻来覆去端详片刻,手指在刀身上轻轻弹了几下:“这把刀应该来自印度。”
裴云飞不由暗暗叫苦,光是在上海查找线索,六组就已经忙得人仰马翻了,怎么又扯到印度去了?正胡思乱想着,小田说了他这个判断的依据,还引出了一段二十多年前的旧事。
1928年春,日本爆出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已创建二十三年、以钢铁制造起家、冶炼出全日本综合品质最佳合金钢的神户制钢所发生一起案件,一块重达四十八公斤的合金钢失窃,而这块代号“037”的合金钢是准备送往美国参加“世界合金钢评比会”的样品!这个案子不但使日本警界感到震撼,连天皇都被惊动了。
这起案件整整调查了一年零七个月,最终未能侦破。为此,“037搜查本部”的本部长亦即总指挥松田引见及该本部下辖的神户组组长大阮初兴自杀谢罪,这二位都是当时日本的名侦探,其中松田引见的事迹还曾被改编为电影。“037案件”被列为重大悬案。
侵华战争期间,小田作为地方技术人员被军方征召,分派至上海,到“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江南造船厂)主持金相研究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一夜之间占领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日本宪兵队对公共租界的外籍巡捕宿舍进行搜查时,在一名印度巡捕的衣柜里发现了一把黑色匕首。日本军曹是学理科出身,对这把黑色匕首很感兴趣,这家伙是懂刀的,弯腰捡起来随手一划拉,竟然削掉了茶几一角。
当下,他给四川北路宪兵队特高课的阿部少佐打电话报告了此事。阿部拿到这把匕首,立即驱车前往江南造船厂作金相分析鉴定。
鉴定是由小田做的,最后得出结论:送检物系采用失窃的“037”样品制造。至于黑色,是在制造过程中添加了某种尚不为人所知的神秘矿石,在高温作用下发生化学变化,冷却后通体变成黑色。经检测比对,原先的母本“037”与这种神秘矿石混合后,能够明显增加钢材的韧性。
刀的主人,印度巡捕奈穆里·希瓦被重点调查,可是,赶到关押外国人的集中营一打听,奈穆里·希瓦并没有关在那里。其时印度、越南未被日本政府宣布为“敌对国”,因此,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印度巡捕和法租界巡捕房的越南巡捕都给释放了,奈穆里·希瓦不知所踪,调查也很快就进行不下去了,那把黑色匕首也被人带回了神户制钢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