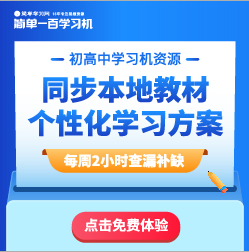9.兵分三路
“我们兵分三路,分头寻找白草圈子。”
被麻向忠这么一耽误,浪费了不少时间。徐库水如果知道有人追踪,拼命坚持,就完全可能最先到达国境线。
唐义不得不下决心了。
汽车已经指望不上。原计划绕着林地走,这也不可能了。也就是说,只有抄近路,才能按时赶到白草圈子。可抄近路,要冒很大风险,他不想让大家冒险,在情况不明时还走个没完,等干粮吃完体力用尽,那就危险了。现在必须分头行动,既要找到村子,又要直插江边,多点追堵才行。
唐义果断地把人员分成三组,想从三个方位直奔边界。
第一组,由张纪书带队,队员由赵永兵、孙长安组成。
第二组,由郭同福带队,队员是林祥和知识分子模样的肖镜如。
唐义带上大个子张圣龙算是第三组。
其他人都为留守人员,以车为大本营,保持活动,防止冻伤。
唐义特别强调不许离开汽车更不许进入密林。注意观察,防止遭野兽袭击。
唐义看到王亚梅站在汽车旁边,抓着红围巾,低着头,神不守舍。唐义已经感觉到,这次雪地追踪,把王亚梅送到了他的面前,明显地她对他有了依赖。但现在唐义还不能多想,更不能表达什么儿女情长,尽管他很想表达。
他安慰自己,等春天到了,再开始吧!
找块平坦的雪地,唐义把那张地图摊开,仔细指给大家看,让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将要经过的路线。具体的安排反复讲了几遍。
第一组,也就是张纪书小组,奔正南方向。这是最短的一条路,不出意外,应该最先到达松阿察河。冬季的河岸两边,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便于观察嘹望。
他这一组居中,带着张圣龙奔东南方向。这是他计划中行动最快的一组。
第二组,即郭同福小组,直奔正东。这一组在最外围,目的是找到白草圈子,那里将是完成任务后最近的落脚点,再也不能让小分队露宿在冰天雪地之中了,发现了白草圈子就联络,没有更多任务。
这个布置是完整的一点两面。如果总体上判断不错,来的方向是西边,计划兜一个大圈奔正南,正好迎头赶上徐库水,这样三个小组的布置一定会达到目的,在找到村子的同时截住徐库水。他要求尽量保持直线行走,时间以三个小时为限,不许超过。然后原路返回,这么计算时间,正是一天的行程。如果发现了目标,放三枪联络,同时可以抓堵或者击毙。
为了完成任务,唐义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头上的天阴沉着,而森林边上已经出现阳光,几绺光线透进来,窥探似的短暂停留,很快又消失了。
风也不烈。似有似无的在脸上经过,像对自己曾有的狂暴表示歉意。
唐义指挥大家对表,整理枪支,挂上干粮袋。他仔细查看,最后说,如有意外可以鸣枪联络,碰上个头大又成群的野兽尽量避开,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出发!”
唐义下达命令。同时,率先奔东南方向迈开了步子,张圣龙大枪一提紧紧跟在后面。其他小组也动身走向雪原。
唐义走了一段路,回头看,小小的留守队伍前头,站着王亚梅,手举着红头巾冲他们不停地摇晃。
唐义不由得站住了。这个人粗心粗的大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男人,少有的,心里奇怪地涌上一股柔软的情感。是雪地,是这场讲不清来由的任务,是留守小队无依无靠像孩子似的身影,还是征战多年而心身疲累的经历,使他体会并接受了这份情感?总之,这份情感润泽了他一直顽强的意志。他摸了下自己粗糙的方形大脸,胡楂子粗硬扎手,再看王亚梅,心里笑了。他知道这是喜欢上她了,不是像以往那样找机会与女人胡闹,是真的喜欢上她了,有那种手捧细雪怕融化消失了的感觉,他不明白怎么会在这种时候产生这样的情感。昨天晚上有意把胳膊搭在她身上,她没拒绝。他早就发现暗中她闪着幽暗光亮的大眼睛,像等待什么事情发生。他想有进一步的举动,没料到火先烧了起来,打断了他急切的向往。
王亚梅还在雪地里招手,他到底忍不住又走回来,把王亚梅拉到一边说,你帮我办件事,起草一份麻向忠死亡经过报告书。
在这个事情上,唐义不知道这样处理是否能行,可能会受到处分,也可能会降职,关几天禁闭,但总得把眼前的任务执行完再说。
王亚梅说,我不会写。
这么说时,她眉眼之间尽是娇嗔之态。唐义放了心,又叮嘱说,千万不要离开车子,就是个人方便也只能在车头车尾。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有个野兽在暗中盯着你,别给它们当了盘菜。
王亚梅拧着头巾角,身子扭过来扭过去。唐义心里别地一跳,真想紧紧地抱她一下。
此时,唐义还不能预料,回到克尔伦场部之后,他们就开始了恋情。那是在春季抢运物资的头一个月,王亚梅病倒了。辛苦加上不适,高烧不退。唐义既要忙于开垦准备,又要照顾她,多亏了自告奋勇的石小芹赶来,帮了唐义的大忙。在唐义办公兼宿舍的小屋里,终于养息过来的王亚梅主动把自己给了唐义。唐义抱着脱得光溜溜的王亚梅,心里激动难耐。也苦了他们,都二三十岁的人,男女之事还很陌生。小屋太小,唐义披着皮袄坐着,任由王亚梅在身上摸索不停。完全是在她的帮助之下,唐义才体验了如何做男人,奇怪的是在那一瞬间,他竟想起了石小芹和徐库水。
但是,他们的恋情并没有结果,王亚梅在春天的第一场荒火中,为救一只突然出现的五彩锦鸡而献身火海。那时她已有两个月的身孕。
那时已有回归的大雁从空中庄严而整齐地飞过,它们勾嘎勾嘎地叫个不停,引得其他鸟群也活跃起来,似乎这春的世界是它们唤醒的。
10.郭同福之死
郭同福带着林祥和肖镜如往东走。
肖镜如个矮腿短,陷进雪里,别人没觉得怎么样,他已经先喘息得像架风箱。他还埋怨说,不该带枪,这又不是打仗。林祥拨开遮挡的树枝在前开路。他回答肖镜如说,不带枪怎么行,最好带上机枪才好,看到成群的野家伙可以试试火力,这步枪打起来能把人急死。
林祥曾在朝鲜战场上打过一次穿插,一个加强营,围上了李承晚军的一个团。他刚把机枪架好,侧翼的攻击枪声就响得跟爆豆子似的。敌人立刻向他这边撤过来,那用意是马上脱离火力网便于组织兵力反扑,哪成想这边架着机枪。参谋长一声令下,他就开了枪。眼见跑过来的敌人跟他的机枪射程跑顺了道,乐得他站起来往前跑了几步,一通狂扫。眼见敌人堆里丢麻袋一般“扑通扑通”往下倒,参谋长连喊两声他也没听见。等仗打完了,他被评上了三等功又得个口头警告。不过他对这个打法挺得意,从此对枪就像对自己的胳膊腿似的一刻不离。现在机枪没有了,这步枪是差点儿劲,不过从克尔伦场部走时,他还是从武装部王助理那儿磨蹭来两颗手雷别后腰上,这么一别腰杆子舒服不少。他甩开大步跟行军一样走得有板有眼,不时把枪举到眼前瞄上一瞄,也不知他发现了什么。
郭同福走在最后边,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注意向东走的方向,不能有大的偏差。
路很不好走。实际也没有路,在树林中穿行。树冠遮天蔽日。不是腿被绊住,就是腰被缠住,像落人了什么陷阱,一挣扎就走不出来,必须别人帮忙才能脱身。走着走着,郭同福就想出了掌握直线目标的方法:先盯住前方一棵高大的云杉作为直线目标,不论如何钻来钻去,只有到了这个目标,下一个目标确定后再走。每次离开目标必用手斧砍出块记号,他担心返回时走错了路,绕在林子里走不出来,那是相当危险的,所以,确定目标的活儿自己亲自动手。
走路是单调的事儿。蹬上一道山脊,满目树林雪原,再过一道结冰的山坳,景色依然。当他深深喘息时,想到这一切全是由他一句话产生,心生懊悔。或许徐库水没跑,是自己大惊小怪了,再不就是徐库水在边界上兜了一圈,感到无望又转回来。石小芹呢?这么匆忙地赶回白草圈子,郭同福判断,一定有个相好的男人在等着她呢,要不然怎么会走得这么急!女人啊!郭同福叹息。自己美如天仙的媳妇那么早就被逼得撞墙而死,要不然,也可赶来相聚;如果她顺从了保长呢?如果顺从了,郭同福还真想不出来该怎么办。
山势变得陡峭了。由于经年累月山水冲刷,山体形成一道道山梁。两个山梁之间是凹陷的谷地,谷地常年积水,长满一丛丛披头散发的三棱草。山梁上满是密集的柞树、糠椴、龙牙木、黄柏树、毛赤杨,强劲的东南季风把它们吹成向北倾倒的“醉林”。阴坡树冠上垂着帘子般的藤蔓植物,这些植物的叶子早就没了,一根根深棕色枝干像筋脉般裸露着,上头悬挂着成串紫红色的干瘪浆果。
“这是什么?”
肖镜如抓了一把;立刻一手的紫红颜色。
林祥说,别乱动它,没准有毒。他看看果实,又拽一段藤蔓下来。郭同福赶过来,伸手捞一把浆果直接按在嘴里,一股清新酸甜的感觉直通心肺,他嚼得满嘴鲜红,把肖镜如看得直瞪眼。郭同福吃了第二把才说,吃吧!别等我咽气了,这是山葡萄,来来尝几个。那口气好像是他家种的。留心看去,类似的植物连成一片。年年岁岁无人收获,一串串熟透了的浆果挂在上面。如果扒开下面的雪,埋在雪里的才最好,又大又甜。三个人吃得急,浆果破碎了,把一张张脸抹得红彤彤的像猴屁股。肖镜如说,装上点回去给弟兄们尝尝,他拿下帽子翻过来,铺上金黄的柞树叶,扒开积雪,揭开暗红的落叶,精挑细选,装满了棉帽兜,再翻过护耳系好帽带。郭同福看他那两条短腿,把棉帽兜拿过来吊在自己胸前。他说,这东西可以醒酒,还可以酿酒。林祥说,也许我儿子那辈能喝上。接着他们又发现了拳头大的秋梨,圆实黑亮地挂在树上,像无数只瞪大的眼睛。林祥摘下来就啃,梨已冻透硬如石头。郭同福说,这东西放冷水里才能化开,吃起来醒酒解困,黑熊最爱吃它,整个吞进去,又整个拉出来,所以地上的梨子不能吃。他又说,别再耽误时间了,得快点赶路,不能在咱们这一路上耽误了。
郭同福他们攀上山后就走得顺了,他们适应了这种地形,就是雪仍然厚可及腰,走起来十分吃力。郭同福想,翻过山梁应该是平地,那就可以在高处嘹望。可山林变得像梦幻一样,地貌都一模一样。翻过一道梁,下一道同样的山梁再次出现,连见到的树和树杈上呆呆蹲守的猫头鹰都完全一样,感觉好像刚刚走过,这很容易让人止步并改变行走路线,许多人闯进密林走不出来都是因为这个。郭同福还算镇定,他有个预感,结果应该就在前头,在前头某一片林子,或是某一道山梁后头。
这时林祥兴奋地说,好了,我看见前头有老乡了。郭同福说,你看准了,别是狼、老虎什么的。肖镜如也说是人的影子。郭同福仔细观察,果然看到密林深处有几个影影绰绰的人影。他说,天助我们,有老乡就有村屯。只要赶上一问就知道我们到了哪里。即便前头不是白草圈子他们也能给指个路。在这大东北的荒原里,见着个人比见着人参还难。
“快追上去问问!”
郭同福打头,三个人气喘吁吁往前奔,还隔着一段距离郭同福就喊:
“喂!老乡请停一停,问个路。”
那头的几个人看样子早就看见他们了,听到喊声全都站住。但奇怪的是都躲在树后隐藏着身形。
郭同福步子大,紧赶了几步,招着手说:
“我们迷路了,打听一下,白草圈子怎么走?”
那几个人没有答话。郭同福以为对方没听清,又喊道:“老乡们——”
刚喊了一声,万没想到对面竟然“当”地打了一枪过来,郭同福应声倒地。林祥和肖镜如立刻卧倒。
对方接二连三射击,打得头上树皮乱飞。林祥抓过步枪就地一滚往前扑了几步,用大树做掩护,边开枪边往前跑。对方并不示弱,开枪还击。林祥从后腰上摸出手雷往树上一磕甩过去,轰地一声,炸起一团枯枝败叶和尘土。对方有些慌张,连放几枪转身要跑,林祥的枪紧跟着来个点射,噗的一声,也打倒一个。另外几个头都不回,像飘似的从山坡上很快就消失了,把林祥看傻了眼,追过去,被打倒的人已经死了。只见他一身黑袄黑裤,但已破烂不堪,下头扎着绑腿,一看就是惯于山林活动。那几个人没有留下脚印,雪地上只留下几条长长的压痕。
“妈的,怎么还有土匪?”
林祥叫道。
是土匪。哪年哪月被打散的不知道。只知道土匪们凭借着边界线上几百里的无人区,踩着滑雪板来去。
林祥在树后找出一双窄长快速滑雪板,不同于一般猎人用的普通板子,一看就知是老手,惯于穿山越岭。
林祥说:“东北剿匪都多少年了!”
肖镜如说:“可能是溃败的散兵游勇,跑到这无人居住的边界地带来,我们一喊老乡他就慌了,再追他们就过了境,还得小心,没准还有个把小股土匪出现。”
他们简单地进行了搜索,确信没有其他情况,赶快过来救郭同福。
可郭同福头扎进雪里,早已没有一点声息。
郭同福参加过的大小战斗有几百次了,凭他的军事技术,几个土匪不在话下。可现在步枪压在身下,一枪没放。帽兜子里紫红的野葡萄被鲜红的血浸透,洒在雪地上,像无数颗惊心动魄的血滴。
11.迷路的赵永兵
张纪书这一路走得挺顺,翻过山坡后林地开始平坦。杂乱的树木混合着茂盛的枯草。这些原产于蒙古草原的冷蒿、针茅草、羊草、小叶樟草,由于蒙古干旱季风的影响,随着风沙,翻山越岭向东扩展而来。
他们走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地势渐渐升高,出现粗大的常青松,上到坡顶才发现松树是林地的镶边,往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柳树丛荒草芦苇杂陈一处,在风中飒飒作响。而松树也变了样子,千百年的东南季风锲而不舍地吹拂,使倔强的松树向西北弯下身躯,不肯服输的树冠却一头接地另一头斜插青天,像靠地迎风放置的巨伞。风来树挡地搏斗了上千年,树冠擎天,而树木之下什么都没有了,季风扫荡了一切。壮观的景色让张纪书有了感慨,这地方该建个公园,老了以后可以在此看看风景。
孙长安说,看风景可以,先得有媳妇。
张纪书逗他说,媳妇不愁,上级从湖南、山东召集来不少,准备发一批下来,让你们挑。
孙长安脑筋不够用,把这话当了真,说,这你得帮忙让我先挑。
赵永兵说,娶媳妇又不是买马。
孙长安仗着自己是老兵,对二十出头的小兵不放在眼里,说,你还是个毛孩子,懂啥叫娶媳妇。
赵永兵说,我当然懂了,娶媳妇就是生孩子么!
孙长安来了精神,说,你知道孩子是咋生出来的?媳妇领进门孩子就自动养出来啦?
赵永兵争辩说,那谁不知道,先大肚子呗!
孙长安更来了精神,说,咋样才能把媳妇肚子弄大你知道么?
这把年轻的赵水兵问住了。是呀!只知道女人会大肚子,可大肚子是怎么来的他没仔细想过。他还不知道世间男女之间会发生人事,没有这人事人间也就不存在了。
看他答不出孙长安很得意。张纪书问,老孙你就懂么?
孙长安自信地说,我怎么会不懂!
孙长安的经历也很特别,原在贵州家乡父母曾给他包办了个童养媳妇。孙长安还记得,媳妇进门时,梳着两条长过腰际的大辫子,下身穿青色肥腿直筒子裤,上身穿件家染碎花小褂。是孙长安的老爹用了二百块现大洋买来的。那年孙长安十二岁,讲定了等他十六岁时给她圆房。那时她十八岁,晚上小俩口住一个床上,他把她当妈了,拱她怀里闻着她甜丝丝的气味。再不就把她当马,骑上去乱喊乱叫。有时她按捺不住撩开他的兜肚摸摸小鸡说,什么时候你才能长大。他不懂还问,长大了干什么?媳妇说,长大了好过日子。他不懂怎么才叫过日子。
等他十六岁要圆房了,个头还没长高。爹手里的钱,都是赌博赌来的,他一生没干啥正经事,赌赢了吃喝玩乐,输了就卖裤子当袄,倒还记着给儿子办事。从清水江乘船到贵定上岸,雇上挑夫到贵阳置办大礼用品。可万没想到东西齐了,亲戚邻里也通知好了,那媳妇却跟上一队过河的马帮走了。溪水边丢下一双棒槌和石板压着的一包衣服,从此杳无音信。孙长安经常会在梦中见到那媳妇,仍然是那一身裤褂,甚至闻到了她身上清甜的香味,醒过来是一场空。也不知道她流落到了哪里,是死是活。那些马帮行无定期,居无定所,每个人都披散着头发、胡子,蓬头垢面,野人一般。一年到头翻山越岭地赶路,常有掉下山涧摔死或遇强盗被砍死的。但愿这些人能对她好,这是他最希望的。不指望这一生再相见了。
他们爬上一道土坎子,站上头嘹望。
眼前是开阔的荒原,蒿草连绵。积雪被风吹成一条条压在草上,更多的是冰凌,草地显得古老荒凉又支离破碎,显示出秋冬季节气候的恶劣。
孙长安说:“我看不用往前走了。”
张纪书看看表才两个多小时,他说,唐队长要求走六至七小时,现在回去最多四小时。索性咱们扩大点搜索范围,我和赵永兵各向东西方向横走半小时,再往回走。你原地返回。这样不到六小时也可以在车边集合。
他们都同意。看看天色仍旧灰蒙蒙的,没有一丝风。这么空旷的地方竟然无风,让人生疑。视野倒是很好,看出去四野清晰,个把小时的路往回走,一点儿不复杂。
分手的时候,张纪书叮嘱赵水兵说,不一定走半小时,稍微横向拉开点儿就往回走,只要不是原路就行。
赵永兵说:“放心,我还有枪呢!有情况鸣枪联络。”
他们招了招手分头走了,反正一两个小时后又见面了,用不着客气。
赵永兵走得很轻快,脚下的冰凌“咔吧咔吧”响得极脆。捡一块含嘴里慢慢融化着,最初的冰凉让舌头发麻。
他感觉走了有半小时,还看不到山林,只有荒原连着荒原。天空的云层很明显的变厚重了。有风,刮得也怪,像被魔鬼指挥着,呼地一阵很猛烈,然后又风息树止,连草梢都纹丝不动。
面前横一道土冈,他打算过了土冈就往北折,向回走,或许土冈那一边还能发现些什么。到近前才知道土冈很高很难爬。他背着步枪手脚并用,分开重重叠叠的山里红,它们托着厚厚的积雪,雪下是白毛一样的尖刺。他小心躲避着,蹬上土冈见到脚下是条河沟,沟边上像等待他似的站着条火红的狐狸,两只狡猾的小眼睛正看着他。他摘下大枪端着瞄准。狐狸竟把脸扭过去,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想起唐义的嘱咐他又放下枪。就像专门来考验他似的,洼地上又出现一群足有二十多只的麂子悠然而过。白屁股在荒草中一颠一颠渐渐远去。
他冲下河沟上到对岸,只见成片的芦苇密实而壮观,簇拥着倔强地立在冰雪中。
他在苇海中穿行一阵,转个方向,他认为这是往回走了。脚下开始轻松,不再磕磕绊绊,是积雪没了,芦苇也消失了,只有半人高稀疏的茅草。风是突然间刮起来的,像是来自地面,卷着细碎的雪粉向天上扬去。突然赵永兵吃了一惊,荒草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冰冻的湖面。赵水兵回头看看,那里是他刚走过的大片芦苇。而芦苇那边什么也看不见。风来得更强烈了,他想好好判断一下方向,湖面远处卷起浑浊的苍白天色,他正犹豫,第一波狂风已经到达面前,那白色原来是狂风卷着天上地下的积雪横扫湖面。
暴风雪来了!
赵永兵知道,平坦湖面上的暴风雪会把强壮的鹿冻透冻僵,何况人呢!再往回走是不可能了,只有想办法躲避。但湖面上什么都没有,平坦得让人无所适从。他看见了那片焦黄的茅草。他迅速解下绑腿,拢住一丛芦苇,把撕扯下来的茅草往里塞。他疯了一样拼命撕扯,手被割破鲜血直流。但他什么也不顾,眼见茅草塞成的地窝成了型。当暴风雪到达时他已胜利地钻进草窝。
风势很猛。它从霍库茨克海发源,经过大陆架到达千里之外的冰湖。冰湖的平坦使暴风雪欢天喜地狂飞乱舞,放任地蹂躏着湖面上的残雪碎草。它让乌云裹上漫天大雪,任意涂改大地,把低洼处抹平,把凸起处埋掉。让大地按它的意志改变模样。好像它喜欢大地,想让大地随它所愿,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到了湖岸边,狂奔的脚步受到阻隔。是那些密实的芦苇携手并肩,好像专为风暴结伴而来,它们繁衍百年,根系盘根错节死死抓住湖岸,把伤痕累累的身躯迎向风暴,而风暴并不甘心,把那些叶片抓住狂摇,让它们发出长长的凄厉的叫声。
暴风雪一连刮了三天。
第一天他还想着张纪书他们,嘴里含着雪水,担心他们没有躲避风雪的地方,如果能找到这里来还可以三个人挤挤。
第二天上午,一只被风刮得晕头转向的五彩鸡,撅着屁股拱进草窝,他抓住了它,看着它美丽而高傲的羽毛,实在不忍心杀死它,把它放在草窝口,它竟然不肯飞走,趴在那里敬畏地看着迷茫的天空发呆。
到了下午,赵永兵开始昏迷,眼前景物时而清楚时而模糊。他提醒自己千万坚持住决不能睡着。可头像被什么按住了,僵硬得不能转动。想起唐义的话,把枪横到面前来,想鸣枪联络。平时的扳机很容易击发,现在显得那么沉重。他并不觉得冷,下肢早巳没有冷的感觉。他努力半天,不是枪的扳机沉重,是手指弯不过来,手指又黑又粗,用牙咬咬毫无知觉。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把枪机扳了一下,枪口贴着湖面响了一声。他随枪身一抖也就放了心,不用着急了,听见枪声唐义张纪书郭同福王亚梅他们会来找的。他想歇一会儿,反正他们快来了,就歇一会儿,就一会儿……
他慢慢阖上眼睛……
当报春的鸟儿开始在天空歌唱,千姿百态的春天真正来临的时候,这座冰湖将是一片汪洋。
那时候,咱们的赵永兵会在碧水深处醒过来,拨开脸上的水草问,春天真的来了么?
可惜,没有人回答。
12.找到了徐库水
唐义带着张圣龙走得很快。他什么也不说,只管闷头赶路。他确信自己这一路应该能找到白草圈子,它不会很远。张纪书这一路是堵住徐库水向西南跑。他知道,密林追踪都是被迫者先发现目标。不等张纪书发现徐库水,徐库水早就改变逃跑方向了,这就给向西插在国境线上留下机会。但关键是他这一路要快。他回头催促张圣龙说:
“我们还要加快!”
张圣龙身长步大,奋勇向前。唐义边赶路边想着,不知道王亚梅怎样写那份报告,对老麻的死他还不知道怎么说。他反复问自己,真的需要开枪么?如果不开枪,老麻会跑到哪里去?唐义始终不明白老麻要跑的正北将是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跑?跑的这么匆忙慌张。
林中出现一条便道,有马蹄子、爬犁的印记从上头走过。
密林中常有零散人家居住,马爬犁是他们的交通工具。但这已是明显的一条山路。弯曲着爬行在山坡树空之中,一时还分不出它来自哪里通向何方。或许它就是通白草圈子的路。一般说来,林中的路必定通到有人居住的地方。
唐义更有信心,催促张圣龙加快脚步。
前边传来清清凌凌的水响。
是一眼山泉,在这严寒之时仍然汩汩流淌。水不断冒出来又不断被冻结,竟形成一座壮观的冰塔,“塔”尖上热气腾腾。脉冲式水流浇到冰面上,发出“咔咔”的进裂声。张圣龙跳上去,想用手捧口水喝,手伸下去,却怪叫一声掉了下来,唐义以为张圣龙被烫着了,抓过他的手,吃惊地看见张圣龙举着的手上却结满冰凌,像蘸好的冰糖葫芦。唐义顺势把他拉倒,手插在雪里,好一通揉搓,直到冰层融化,手上泛出血色。
唐义找根树棍,从泉眼探进。泉水清澈,树棍上的青苔像被加热了似的冒着气泡,当把树棍提出来,刚脱离水面就结一层薄冰。厉害!唐义吃惊不小。水喝不成,吃冰块吧!张圣龙敲打下一根透明的冰柱,没等送到嘴里就被唐义打落。
“只能吃雪解渴!”
“为什么?”
“冰块会粘在舌头上。”
张圣龙只好再次放弃,绕过山泉继续赶路。
唐义抓把雪,按在大汗淋漓的额头,顺手划拉两口雪咽下去,透心的凉,让他忍不住大张着嘴换气。这时,他发现跑在前头的张圣龙,像遭遇了什么意外,突然站住,往后倒退几步,然后捂着嘴跑到一边。
唐义习惯地掏出枪赶过去。没等走近,他一眼就看出,那在路边上躺着的正是他们追捕的徐库水。
但他已毫无生息。
唐义横移两步,看到徐库水左手抓着木棍,右手握着日军枪刺,仰面朝天躺着。棉帽子掉在十几步外。
雪地上一大片杂乱的人与四条腿动物的脚印,看得出,这里发生了很激烈的搏斗,脚印从四五十米外开始混乱,一直延伸到路边。徐库水无疑被狼群围住了。狼足有二三十条,围了有两三层。看样子徐库水曾试图突出包围,但没成功。最后的机会是眼前这棵大树,他想爬到树上,及时跟进向上跳起的母狼成功地制止了他,树杈下留下几绺棉絮。落地后,他发起最后一搏,最先扑上来的年轻母狼吃了致命一刀。树下有条支离破碎几乎只剩一张皮的狼,是徐库水成功反击的证明。但他打赢了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个战役,他的肚子被狼撕扯开,肠子细线一样拖在地上。下边两条腿没有了,咬烂的棉裤被狼吐得一团一团的。
触目惊心的现场让唐义站了半晌没说话。他在想,跑啥呢?这么匆忙慌慌张张!你是有什么心事?要躲避什么?不是刚到克尔伦么,日子长着呢!
张圣龙捂着嘴干呕了半天,站远远的不肯过来。他是武汉军校的学员,还没见过这么惨的死亡。
去砍些树枝来。唐义说。
桦木条很软,几根绑在一起就是担架。徐库水已变得短小,唐义把他收拾一起,用茅草卷成筒状绑好放上担架,用绑腿系住担架一头,当作爬犁拖着往回走,听到有狂风从树梢上掠过,西南方向好像变天了,这让他很担心。
原路返回走得挺顺利。事情结束了,什么也不用想了,现在要把队伍集合起来,尽快带回克尔伦去。
远远地看见了汽车,也看见了王亚梅,她跪在地上。周围人肃立不动。
走近了才看到,王亚梅正在用白雪擦拭郭同福脸上身上的血迹。不时有紫红的葡萄从郭同福怀里滚落,每掉出一颗葡萄来,王亚梅就叫一声郭同福的名字,她以为那是血,以为弄痛了他。
这时的郭同福,脸上的表情安详而平和,什么痛苦都没有了。徐库水也好,王克也好,克尔伦场部也好,都与他无关了,连同他在旧军队的经历,以及不知如何书写的“自传”,都彻底永远地结束了。
唐义让大家站成一排,脱帽鞠躬。
张纪书说,把他们全埋在这儿吧!砍上一棵松树做个记号,开春后再说。
唐义点头。
张纪书汇报说赵永兵还没回来,唐义问大家听到枪声没有,都说没有。
这样一来,队伍还不能撤回克尔伦,只能尽快赶到白草圈子,到那儿之后,再组成搜索小组,寻找赵永兵。他让林祥用三根木棍在车厢板上绑成箭头,又在驾驶室里放了袋炒面。或许赵永兵能自己走回来,有袋子干粮就能坚持下去。
王亚梅攀上车,把自己的红头巾高高地绑在车上,希望能让远处的人看到。
唐义举起手枪,冲天连开五枪。砰砰的枪声顺山林传出很远,随着枪声渐远渐落,林中传来“嗒嗒”的马蹄声。意外的马蹄声令人紧张,林祥、肖镜如刚才的遭遇让他们不敢大意,他们边抓枪在手边招呼大家隐蔽。
但已不用隐蔽了,来自白草圈子方向的马爬犁闪出树林,马喷着白气,浑身冰霜。马爬犁上除了赶马的老板子外,还有一个穿大红袄的娘们儿,山风吹得脸蛋像红苹果,她神采飞扬地来到近前,先大惊小怪地喊道:
“哎哟!你们咋跑这儿来了?”
大家这才看清,是房东小媳妇石小芹。
不等大家答话她又说:
“不能停在这里,暴风雪已经在冰湖上刮开了,这里的天气老是这样没有准数。”
她环顾四周,像突然想起来似的喊道:
“怎么么没看见徐库水呀!他说今天要赶到这里接我的,一路上过来怎么没见他人影呀?”
13.尾声
在克尔伦场部,小黑板上写着:
今天最低气温零下四十二度,局部地区有大风。请各单位外出人员注意防寒,未经批准
不得野外宿营。
下边还写了一段气象知识:
克尔伦镇处在我国最寒冷的地域内,气温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来自寒极附近的东西伯利亚寒潮气团,夹带上号称太平洋冰窖的鄂霍次克海产生的季风,长驱直入,横扫欧亚大陆的最东端,直袭三江平原。从日本海附近的小笠原群岛,扑过来一支海洋性暖湿气流,它们在克尔伦所在地区上空相遇,两强相遇勇者胜,现在北风势大力沉,风雪天气在所难免。但南风不甘示弱,又使北风不能顺畅过境,风雪天气必会一阵大一阵小持续不断,经三五天后才见分晓。然后天空晴朗,气温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