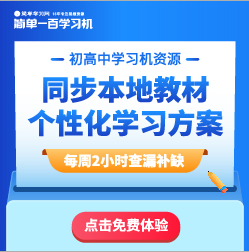六、线索突现
9月24日星期六这天,轮到柯传珠值夜班。公安局的夜班值班主任有一項再忙也必须在午夜前完成的工作:审阅各分局在当晚十点前送到市局的通报材料中治安口的内容,午夜前送交局办公室;局办值班人员将治安口材料连同政保、交通、消防材料汇总,分门别类打印,次日上班前由机要通信员分发市局各部门和分局。
柯传珠在审阅当天徐汇分局送来的治安材料时读到一则情况,若换了其他人,可能就忽略了,但这则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
徐汇看守所一个月前收押了一个十七岁的盗窃犯邵健康。当时人们普遍钱袋瘪塌塌,失窃的钱钞数额一般都不大,也少有怀里揣着一沓钞票去购买金银珠宝的,“家电”这个词儿仅仅指的是收音机、手电之类,整个儿社会包括公安局在内都管扒手叫“小偷”,其中这个“小”字也从侧面说明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经济状况。小偷被抓到,处罚也很轻,如果家庭出身是劳动人民,头三次一般不会逮捕判刑,关几个月就放了;三次之后再犯,那就升级到劳教(少教),一般都得折腾数年方才轮到判刑吃官司。
这个邵健康还是第一次失风折进局子,以为自己要送少教,吓得哭哭啼啼,还不肯吃饭。看守员找他谈话,得知其绝食原因后,当然不会说你别担心,关一段时间肯定会放你回家,而是宣传“坦白从宽,将功折罪”的政策。邵健康急于立功,向看守员坦白,他曾听一起逃学扒窃的小伙伴林星儿说过,不久前曾帮人藏过一件稀世文物。这文物稀奇到什么程度呢?全上海只有一件那是肯定的,全中国全世界恐怕也屈指可数!看守员在工作中碰到这种满嘴跑火车随口胡扯的情况多的是,当时也没太在意,但作为工作内容,还是在值班记录上写了一笔。
两天后,看守所新任所长老方上任,翻看值班记录时注意到这个情况,立刻提审了邵健康,问明林星儿的住址后,形成一份材料转给分局治安科。治安科就派民警老魏、小陆去找林星儿谈话。按照老规矩,那二位没直接登门,而是去了管段派出所。派出所方面介绍,这个林星儿是派出所的常客,平时打架起哄聚众闹事件件少不了他。接着就打电话给居委会,让通知林星儿到所里来一趟。老魏、小陆等了半个钟头,没消息。户籍警小钟再给居委会打电话问是怎么回事,放下电话,小钟的神情有些古怪,说居委会接到电话就通知林星儿了,而且看见他出门朝派出所方向走来了,按说几分钟就能到,但现在……看来这小子心里有鬼,脚底抹油开溜了!
三人立刻去林星儿家,其外婆说孙子刚才接到居委会通知,出去后就没回来过。老魏、小陆没招儿了,只得回分局报告,挨了领导一顿批评。治安科认为既然林星儿开溜,那说明邵健康检举的情况多半是确实的,这需要引起重视,于是通知派出所安排管段布控。
柯传珠看了这个情况不由得寻思,林星儿替人藏匿的会不会就是顾训实失窃的那块灯明石?如果是的话,那倒是一条很好的线索,顺藤摸瓜没准儿就能把这个案子给破了。他把这个情况编进了当天的通报材料,看看午夜将至,正要送往局办时,忽然接到徐汇分局的电话,说那个林星儿已经抓到了,请把那条协助追捕的信息从送审材料中撤下来。柯传珠很想知道林星儿替人藏匿的究竟是不是顾训实失窃的那块灯明石,但公安工作有纪律,他不好打听,只得忍住好奇心,把该信息撤下,把材料送往局办。
这天下半夜出奇地清闲,全市竟然没有发生上报市局的治安案件,柯传珠原本可以打个盹儿,可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灯明石。9月25日上午八点半,交班时间到了,不知怎么,柯传珠没来由地觉得林星儿已经把藏匿灯明石之事交代了,徐汇分局报告市局了,市局领导决定重新启动侦查,那多半儿还会让他主持专案组。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柯传珠交班时下意识地磨磨蹭蹭,比平时多花了至少十分钟。可是,直到九点多他骑着自行车出了市局大门,也没见有什么动静。
柯传珠家住虹口,从市局回去骑车大约半小时,还没到弄堂口,传呼电话亭的阿姨远远看见他就扯开嗓门儿喊:“柯同志,你们单位来电话叫你立刻回去,有急事!”
柯传珠掉转车头便奔市局,寻思定是领导决定要恢复侦查灯明石失窃案的专案组了。他猜对了一半——治安处领导告诉他,徐汇分局报告,6月下旬全系统内部通报过的那起“6·20”案件中失窃的赃物有了线索,市局领导认为有必要弄清楚该线索是否有价值,指令原专案组长去徐汇走一趟,当面讯问嫌疑人,然后视情行事。柯传珠相信,这个决定肯定与博物馆向市公安局发的那份公函有关。
任务交代了,领导又对他说,老柯你昨晚值夜班,还没休息,先回去睡一觉,下午再去徐汇也不迟。柯传珠嘴上答应,心里已经急不可耐,恨不得把自行车换成摩托车立马奔徐汇。领导像是猜到了他的心思,干脆开了条子,让他去取一辆两轮摩托。
在徐汇分局,柯传珠提审了林星儿。林星儿那年十六岁,个头儿比同龄少年瘦弱些,脸色蜡黄,像是长期营养不良的样子。跟他聊了个开场白之后,柯传珠却暗吃一惊:这少年出身富家,其外公解放前是上海滩有名的资本家,现今已八十多岁,身体依旧硬朗,公私合营后每月光定息就可拿上万元。少年之母是外公唯一的女儿,寡妇,领着林星儿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不工作,全职照料二老,但家里雇着两个保姆,她无须干什么家务。此外,外公每月另给其女开一份薪水——一百零八元。林星儿吃穿都是外公供给,外婆每月给他三十元零用钱。因此,林星儿是当时上海滩为数不多的饕餮一族,个子矮小脸色蜡黄,那是生相,其外公也是这样一副长相,活到八十多岁了啥毛病也没有。
林星儿比较健谈,看样子还想继续闲扯,柯传珠说咱们言归正传,昨晚你进来后,承认替别人藏匿过一件文物……话没说完,却被林星儿打断:“这事我只和市局领导说。这位同志你难道是市局领导吗?市局领导是黄赤波,我知道的,也见过他。上次黄赤波到龙门路派出所检查工作,当众训斥副所长,我正好在派出所关着,亲眼目睹,你别想蒙我。”
柯传珠只得说:“我就是受市局领导的委托来找你的。你说到的情况牵涉一桩不小的案子,我相信跟你无关。如果你说清楚呢,马上放你,我用摩托车把你送回家;要是不说,那就只好一直关着,关到我们把案子查清再说。”
林星儿还是知道轻重的,看守所这地方,呆久了也确实没意思,于是就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
林星兒跟邵健康一样,也是一个只想玩耍不想读书的少年,逃学、打架、偷窃是家常便饭。最后一项只是为了寻求刺激,他每月三十元零用钱,比一个普通工人一月的工资都不少,况且不够的话还可以向大人要。可能是因其外公的名气,林星儿在外面折腾时,大小混混儿都愿意结识他,所以他就有了许多老阿哥、爷叔、伯伯甚至爷爷辈分的朋友,辈分越高的,对他越是客气,一口一个“林少爷”,有时正好在马路上遇到他,还会请他吃冷饮、吃点心,或者送戏票电影票。这于他是一份很大的面子,而且还有实惠:凡是打架现场,只要他一露脸,对方那帮家伙不管已经占了多大的优势,都会自动停战,道声“自家人”,立刻离开。
6月下旬的一个阴雨天,有一个绰号“阿胡子”的爷叔在电影院门口遇到林星儿,问林少爷你看完电影有事吗?没有的话,我们到“光明邨”搓一顿怎么样?林星儿这几年里受到的类似点心、饭局之类的邀请比较多,不过他跟“阿胡子”不熟,“阿胡子”以前也没单独请过他。现在,“阿胡子”请他下馆子,估计是有事要他帮忙(林星儿最擅长的就是利用他和多方混混儿都熟识的关系从中传话、调解矛盾)。能受到“阿胡子”之流的重视,满足了林星儿的虚荣心,于是,电影散场后他直接去了“光明邨”,“阿胡子”已在门口等候,并订了一副双人座头。
“阿胡子”宴请林星儿果然是有事相求,但不是要他做传话筒,而是请他相帮“办一桩小事”,把一件东西放到家里去就是了。林星儿打自十一岁开始混江湖,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他认为这真是小事一桩,不就是把一样东西在自己家里放一放吗?林星儿当然知道这不会是好事儿,家里大人肯定是不能知晓的,所以,他要问清楚放的是什么东西。“阿胡子”说是一块石头,他也是受人之托,可既然答应人家了,就得做妥当。石头不大,但人家关照,一定要“阿胡子”亲自去摆放才放心。
这个似乎就有难度了。虽然在外面林星儿被朋友们平等看待,给他面子,但在家里不过是小孩儿一个,不但外公外婆老妈要管他,连两个保姆都可以对他发号施令。而且因为派出所不时会“麻烦”他,家里对他也有约束,比如不许把同学朋友领到家里来——有一次学校老师去家访,保姆不认识他,就把老师拦在门口,脸色也不大好看,弄得老师很尴尬。后来外公出来问明白了,老师才得以进门,调侃说贵府真是侯门深似海啊。所以,“阿胡子”想亲自上门寄存东西的主意只怕没得打。
“阿胡子”说这没关系,爷叔我自有章法。林少爷可能没听说过爷叔是干啥行当的吧?哈哈,爷叔是钢琴厂的修理工,专门修理钢琴。我十四岁学生意,跟的是英国师傅威尔逊先生,那是上海滩有名的钢琴修理师,到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不是我吹牛,上海滩目前能修理解放前外国老钢琴的技师里,爷叔我绝对可以排在前十位。
林星儿家里是有钢琴的,不过他不大弹,主要是老妈弹,而且每天早晚都要弹一阵。“阿胡子”听林星儿这样一说,主意马上就来了。他告诉林星儿,只要在钢琴的某个位置稍微做一下手脚,让钢琴出点儿小问题,你妈妈肯定会给钢琴厂的修理部打电话。全上海修理钢琴的技师技工有不少,但修理部独此一家别无分号。我查过修理记录,你家以前修理、调试钢琴都是找我们修理部,只不过不是我出马。这次爷叔会留意,亲自出马维修,到时候我会把东西放进钢琴里。至于放到几时……我是受人之托,也说不准,反正要取时事先会告诉你,到时候你再在钢琴上做一下手脚,我上门维修时取出来,还不是易如反掌?
林星儿听着频频点头,只有佩服的份儿。“阿胡子”喝了几杯酒,话多起来,他向林星儿透露,朋友说这块石头是他家祖上留下来的,十足的老古董,别说全中国了,只怕全世界也只有这么一块。林少爷你平时要给爷叔多加留意,我来修理时会在钢琴后面某个位置留下“孟轧”(英语“记号”的洋泾浜谐音),如果你发现动过了,要马上给我打电话,我会紧急处置的。然后,“阿胡子”自吹自擂了一番,说上海滩道上没有他搞不定的事,以后林少爷有啥事情需要帮忙的,只管开口。
林星儿具有叛逆少年的共性——对家人的教诲置若罔闻,但对外人的说词却容易全盘接受。他很乐意结交“阿胡子”这个了不起的大朋友,这件事很快就按照“阿胡子”的策划圆满办妥了。
不过有一点是在“阿胡子”的计划之外的。尽管他关照过林星儿要对此事守口如瓶,但要让一个尚不通世事的少年、尤其是林星儿这样的主儿做到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犯难的,除非将其隔离起来,不让他跟外界打交道。林星儿是个待在外面比蹲在家里的时间多的溜腿儿,大人对他的评价是“猢狲屁股坐不牢”,而他只要外出,就肯定要会朋友,会朋友就要吃喝,诸如冷饮店、点心店之类,有时兴致来了,还要下馆子喝酒。遇到谈得来的朋友,两杯酒下肚,难免信口开河,牛皮一个吹得比一个大。有一天,林星儿和好友邵健康一起在长乐路大胜饮食店喝啤酒,两人对着吹牛,最后就端出了帮人藏匿一块稀世玉石的秘密。没想到邵健康扒窃落网后,为将功折罪向警方检举了此事,导致林星儿也折进了局子。
更让柯传珠感到庆幸的是,据林星儿说,“阿胡子”尚未取走那块灯明石,也就是说,稀世玉石还在林星儿家的钢琴里藏着!
柯传珠问林星儿:“那个‘阿胡子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
林星儿摇头:“这个我不知道,我叫他爷叔,他的工作单位是钢琴厂修理部,你们公安局一查就可以查到的嘛。”
回到市局,柯传珠立刻向领导汇报了提审林星儿的情况。领导说已经跟卢湾分局讲好了,抽调三个原专案组侦查员归你指挥,负责往下的收尾工作,需要什么可以跟分局联系。柯传珠立刻赶到卢湾分局,那边三个刑警钟俊、戴文萃、陆抑川已经在等着他了。当下几个电话一打,立刻锁定了“阿胡子”。此人名叫姜圣行,三十八岁,系钢琴厂修理技师。
当天下班前,主管技术的副厂长借口请教一个技术问题,把姜圣行唤到厂部。“阿胡子”不知这是圈套,对着那份全是英文的老图纸侃侃而谈,还没谈完,刑警进来了,宣布将其拘留,押解卢湾分局后随即进行讯问。
姜圣行供认,确实让林星儿帮忙在林家钢琴里藏匿了一块石头,但石头不是他弄来的,他不过是受人之托。那么,是谁托他的呢?“阿胡子”说出了一个名字——储金富,随后交代了储的基本情况以及和他的关系。
柯传珠记性好,一听这个名字马上想起来,已故老匠人柳耿耿的儿子向专案组说起过,其父生前上百个徒子徒孙中就有储金富这么一号,目前,储是黄浦区连云路房管所修建队的工匠。看来,顾家客堂地下藏有财宝的信息的确是从柳老头儿那里传出去的。
担心夜长梦多,先去林宅起获赃物要紧,柯传珠决定把储金富往旁边放一放,请示领导调了辆中吉普,把姜圣行带上直奔静安区新闸路林宅。哪知,还是晚了一步!
七、大案告破
这天上午九时许,一支由红卫兵和工人组成的四十余人的队伍来到林家,宣布抄家,被抄的物品中就有那架“佩卓夫”钢琴。造反派显然是有备而来,特地开了一辆大卡车,一上来就把林家的大小五只沙发、一架钢琴搬上车运走了。
运往哪里?“淮国旧”——老上海都知道,这是“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的简称,乃是全上海最大最有名的一家旧货商场。“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造反派把抄获的东西送交到各区指定的地点,这种临时处所大多面积有限,也是临时从各单位抽调来的管理人员对大件物品非常头痛,几天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干脆送“淮国旧”去吧。
报市里批准后(当时还未“夺权”,仍由“人委”即市政府辖管全市各个行业),上面一道命令下来,“淮国旧”立马照办。“淮国旧”面积很大,不但有宽敞的店堂,还有多座库房以及露天堆场。于是,市区抄获的钢琴、家具等大件物品就直接送到了“淮国旧”。卡车到那里卸下物品后,由区里指派在那里负责登记的人员出具一纸收条作为凭证就是了。
那架藏匿着灯明石的钢琴被送往“淮国旧”时,林星儿正在接受柯传珠的讯问,两人都不知道石头已经转移地方了。现在,听林家说钢琴已被抄走,刑警倒也并不紧张,既然有去处,那就好办。
这时已是晚上,不过,1966年8、9、10月期间,“淮国旧”应该是沪上营业时间最长的商店,没有之一。该店通宵有人,因为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是没有上下班时间的,半夜袭击也是常事,抄到的大件无处堆放,只有立马送“淮国旧”。可是,上海滩这么大,被抄家的又那么多,“淮国旧”的面积再大,存储能力也是有限的。为保证源源不断送来的大件物品堆放得下,就得搞一边进一边出。出到哪里去?这个店方有经验,原本就是旧货商店嘛,“出”就是出售。当时权力还在市人委手里,一紙报告打上去,立马获得批准:允许把抄家物资作价出售,供广大市民选购。
当时“淮国旧”出售大件,不问牌子、质量,钢琴一律三十元到八十元一架;沙发二十元到四十元一只;红木家具拆零卖(整套没人敢买,担心运回家前脚进门后脚就引来红卫兵“破四旧”),最便宜的鸭蛋凳只要付两元人民币就可以拿走。
用柯传珠事后的说法,如果他知道钢琴要被抄走,那肯定在上午讯问过林星儿后就立刻去林家起赃了;如果他知道“淮国旧”在搞“有进有出”,肯定马上一个电话追过去,让“淮国旧”指派专人寸身不离守着这架“佩卓夫”钢琴。可现实就是现实,没有如果。当几位刑警带着姜圣行驱车赶到“淮国旧”准备辨认钢琴时,店员告诉他们,那架“佩卓夫”上午送来,下午一点多就被人买走了。
刑警大惊:“啊?这么热门儿?”
那店员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一看就是吃了一辈子旧货饭的老法师,他拍拍刑警的肩膀:“朋友,这是‘佩卓夫,世界名牌,八十元就能搬走,懂行的谁不想要?”
“是什么人买走的?”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是吃了晚饭才来上夜班的,那是日班的人经手的。”
“那么,请把流水账拿给我们看看好吗?上面应该有记录的。”
店员陪同刑警去账台,一边出示流水账目一边嘀咕:“你们没法儿查清的,国家规定卖掉旧货要凭工作证或者户口簿,但对买家没有规定,张三李四阿猫阿狗谁都可以买的。我们只认人民币,钞票拿出来东西拿了走,为人民服务嘛。”
店员说的是实情。柯传珠和另外三位刑警匆匆商量下来,认为案子到这一步了,还是先把那个储金富逮住,其余事情再作计议。于是,他们驾车把姜圣行送进卢湾看守所,然后驱车前往连云路派出所,储金富家住新城隍庙,乃是该所管段。派出所方面说辖区有这人,是个中年工匠,浦东三林塘人,精通泥工木工,是本地段房管所有名的泥水木匠,平时没有劣迹,是个守法良民。刑警说只怕最近不守法了,先把他控制住再说。
储金富到案后,起初一问三不知,说自己跟任何违法犯罪向不沾边儿,刚才你们不是已经搜过我家了嘛,有什么赃物吗?共产党讲究实事求是,你们公安局办案子要凭证据的!刑警说没有证据哪能抓你,你先坐着别啰唆,证据稍等就到。一会儿,姜圣行押到,哭丧着脸说阿哥啊,事情穿帮了。储金富恨恨剜了姜一眼,摇了摇头,只得交代了盗窃灯明石的经过——
诚如之前专案组的估料,灯明石的信息是柳耿耿透露的。当然,柳老头儿不知方砖地下藏的是一块稀世玉石,只说肯定藏有东西。这老头儿匠人出身,一手泥工活儿出类拔萃,鲜有人及,为人倒是厚道,就是嗜酒,喝了酒喜欢自吹自擂。他的徒子徒孙、江湖朋友逢场作戏起哄奉承,老头子就吹得愈加来劲。顾训实家客堂方砖地下藏有东西的事,就是他在酒桌上吹牛吹出去的。为表明自己本事了得,他炫耀说,也就是帮小孙子抓麻雀钻到顾家客堂的八仙桌下面趴了趴,不过几秒钟工夫,他就察觉到有一块方砖是做过手脚的,联想到主人是海归华侨,而且世代经商,叶落归根时肯定携回不少金银财宝,出于安全考虑,只有藏在地下最牢靠。
当时在场的就有储金富。别人听了也就听了,只当老头子喝多了老酒信口胡说,只有储金富知道师傅本事了得,因而认定顾训实家客堂八仙桌下肯定有名堂。起初他倒没有行窃之心,储金富虽然算不上有钱,但与老婆两个的工资加起来百二十元,只养一个女儿,小日子过得也算不错了。可是,储金富有个不良嗜好,喜欢寻花问柳。他在房管所修建队工作,每天做的就是拿着报修单跑来跑去查看居民报修情况,然后带领工匠上门修理,也算一个小头目。这工作使他结识了许多异性,难免遇上些轻骨头妖娆货色,七搭八搭最后搭到床上。然后,储师傅就要破财了,买这买那,不答应就以向房管所领导反映、检举相要挟。
这种情况储金富遇到过不止一次,好在不是常事,他在经济方面还能承受。没想到进入1966年,接连遇到两个老阿姨都是这路货色,储金富简直怀疑她们是旧社会玩惯了仙人跳的,既贪婪又冷酷,要钱要物一而再再而三,迫使他不得不举债度荒。借的债一时还不了,就去赌博,想赢了钱钞还债。但事与愿违,连赌数场,场场败北,从此色债赌债,债台高筑。无奈之下,他就想到了顾老先生家客堂八仙桌下的方砖地。
以前柳耿耿在世时,储金富经常去顾家宅,虽然没有进过顾训实的家门,但对顾家的房屋位置了然于心。6月19日清晨,储金富蹬着自行车去顾家宅遛了一圈,想看看那里的情况是否有什么变化。当时他还没有下决心作案,毕竟很难碰到那么巧的事,让他正好有作案的机会。没想到那天运气特别好,他经过顾家门口时,顾谦一夫妇正拎包出门,跟邻居阿婆打招呼说要去青浦白相,今晚不回来了,阿爸姆妈去苏州也还没回来,如果邮差送报送信,麻烦阿婆代收。储金富当下窃喜,暗忖今晚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回去之后,储金富立刻着手做准备。对于储金富这样一个能工巧匠来说,要撬开一块方砖当然不成问题,但必须做到不惊动邻居,那就需要动一番脑筋了。不过这也难不倒他,毕竟他以前学生意时经常给东家撬方砖铺方砖,熟能生巧就有办法了。他去五金商店买了一打两毫米直径的钻头,配上平时做木工活儿时常用的手摇钻,就可以做到基本无声操作。
当天午夜,储金富又来到顾家宅。毕竟是第一次作案,他有些紧张,不敢贸然行动,躲进顾家斜对面的弄堂口观察动静,意外发现有两条黑影从顾家悄无声息地溜了出来,鬼鬼祟祟离去。储金富愣怔片刻,方才意识到那是比他先下手的窃贼,不禁沮丧。想想不甘心,便大着胆子潜入顾家,想着捡点儿漏也是好的,贼不走空,总不见得白跑一趟吧。不料进门后发现客堂里的方砖地完好无损,那两个窃贼并未撬开地面,估计他们不知道主人藏宝之事。既然如此,那就别客气了。他先用手摇钻把那块方砖四周的缝隙钻松,再用尺余长的精钢撬棒轻而易举把方砖撬起,往下挖掘填充物就容易了,总共也就用了二十来分钟时间,就把底下那个盒子取了出来。
携赃物离开现场,回家打开一看,竟是一块石头!这让他有点儿泄气。转念一想,既然主人把这块石头埋于地下,肯定是一件难得的宝贝,也就释然了。不过,这个情况导致他不得不改变计划。
之前他一心以为地下埋的必是黄金珠宝之类,那是有办法兑现的。邻近上海的苏南、浙东农村,男女婚嫁流行互送黄金首饰,储金富认识几个专门收购老货的温州人,原想马上就能出手,根本没考虑过藏匿赃物之事。没想到偷到手的是块石头,温州人肯定不要的,那就只好先藏着,待打听清楚行情再作计议。那么,藏在哪里好呢?家里肯定是不能藏的,只有放到外面某个绝对安全之处。一连想了三天,他终于想出一个自认为稳妥的法子——通过修钢琴的连襟姜圣行把石头秘藏于某个富家的钢琴内。
储金富跟连襟一說,姜圣行一口答应,而且根本没问石头的来源。于是,灯明石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藏进了林家的那架“佩卓夫”钢琴内。最近这段时间,红卫兵到处“破四旧”抄家,储金富担心林家的钢琴被抄掉,正想让姜圣行找个由头上门把东西取出来,不料还没跟姜圣行联系上,事情就穿帮了。
听了储金富的供述,刑警马上就想到了一种可能——储金富发现钢琴被抄走,继而跑到“淮国旧”花钱买下来,于是对储金富当天的活动情况进行了调查。储金富那天上午和另外两个工匠在居民家筑漏,一直忙到午后一时许才一起回到单位。三人去食堂匆匆吃了午饭,又参加了房管所临时举行的政治学习活动,直到下班才离开。这样,就排除了储金富买下钢琴的可能,往下,只有另外设法查找那架钢琴的下落了。
9月26日,柯传珠等四刑警再次去了“淮国旧”,这回见到了经手出售那架“佩卓夫”钢琴的店员老周,还找了收银员钱丽霞。老周说昨天下午来淘钢琴、家具的市民不少,他们七八个负责这一摊旧货的店员忙得不可开交。由于情况特殊,顾客选购旧货的具体过程也跟以往不同——进门后直奔后面的露天堆场,那里钢琴、家具都是分类堆放,供顾客挑选。也有顾客在选购过程中征询店员的意见,但店员实在太忙,只好一律摇手拒绝。老周记得当时正好有红卫兵送来一卡车抄家物资,他立即拿过木板夹,准备登记后出具收条,却被看中那架钢琴的顾客一把扯住了要求开单子。这是不能拒绝的。他还记得,在开单子时该顾客朝那架钢琴的方向扯开嗓门儿喊了一句:“阿三头,你在这边看着,别让人家来抢这架琴,我去付钱!”老周开了单子后,那人就匆匆跑到前面店堂去排队付款了。
至于那人的年龄和外貌,老周已经想不起来了。在刑警的反复启发下,他才用不确定的语气说那是个中年男子,比较瘦,上海本埠人,一张脸有点儿长,肤色稍白,穿一件短袖府绸衬衫……再详细就没有了,连编都编不出来。刑警再去问收银员钱丽霞,那是一个戴眼镜的三十余岁的妇女,她更是连连摇头,一问三不知。目睹现场的忙碌情景,刑警对于她的摇头表示理解。那么,单子和发票上有什么说法呢?没有,那上面只记录着“钢琴/1/80元”。
店员无法提供什么线索,还有其他办法吗?众刑警商议片刻,又想到了运输环节上。顾客买了大件物品,必须动用车辆才能搬回家去。一般的家具可以使用黄鱼车、板车,只要捆扎妥当,不掉下来就行了。这个方式用于运送普通钢琴也勉强,但运送“佩卓夫”那样的钢琴不行。那是立式高背钢琴,不但体积大,而且非常娇贵,顾客通常都是带着几床棉花胎进行包装处理,以免钢琴在运输过程中被损坏。既然如此,那个顾客在把钢琴运走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运输工具呢?这个,就要去询问在店堂内外终日转悠、专门负责防盗和维持秩序的商店工作人员了(现在称为“保安”)。
为应付“破四旧”造成的繁忙局面,“淮国旧”临时聘用了多名保安,大多是原旧货行的退休人员,也有少数社会青年。刑警跟多名保安接触下来,终于找到了一个留意过此事的高姓老头儿。高老头儿是“淮国旧”的退休人员,对这一行很是熟悉。正因为熟悉,所以老高一眼就看出那是一架世界名牌钢琴,这在抄家物资中的出现率较低。他当时还对那个顾客说了一句:“这位朋友,你眼力不错,运气更好,八十块钱竟然淘到了一架‘佩卓夫!”老高记得,那架钢琴是用卡车运走的,卡车的驾驶室门上喷印着“上钢八厂”的字样。
这就可以继续往下追踪了。刑警当即赶赴武宁路桥堍的上钢八厂,打听到买钢琴的顾客系该厂工程师张亮。张亮说钢琴是给儿子买的,运回家后还没动过,已经联系了调音师,说好今晚上门调试。刑警终于松了一口气,很快,在张家起获了藏在钢琴里面的那块灯明石。
稀世玉石失窃案的侦查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1967年2月3日,案犯储金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陈培笙、蒋才峰、姜圣行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到十年不等。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