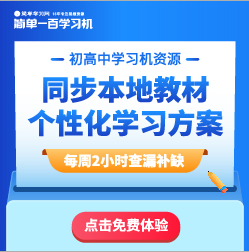三、“无形一炷香”
大约二十五年前,江南黑道上突然冒出了一个行窃高手,自报匪号“无形一炷香”。自1926年到1942年这段时间里,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杭州这六个江南名城,每年都会发生一起盗窃重案。案件情节高度相似。作案目标必是高官或富商的宅邸;行窃的时间清一色是下半夜1点至4点。下手过程更是匪夷所思,连每年必定摊上一起案件的上述六个城市中刑侦力量最强的“首都警察厅”最有经验的老干探,也弄不清案犯是怎么进的现场,反正事后勘查时,门窗的锁具插销完好无损,围墙、房顶也未发现攀爬痕迹,至于足迹、指纹什么的,就更不用找了——人家号称“无形”,离开现场前肯定会把这些痕迹清理干净。
那么,遭窃对象难道没有任何察觉吗?是的。请注意人家报出的匪号,“无形”后面还有“一炷香”三字。在神不知鬼不觉潜入作案现场后,窃贼必会点上一支特制的迷魂香。这支香的长度和粗细也无人知晓,这些灰烬自然也不会留下。尽管如此,根据失主的描述,也可以想象到这位高人使用的王牌作案工具的厉害:下半夜所有失主都是沉沉睡去,什么动静也不知道,拂晓时分远近此起彼伏的公鸡啼鸣声根本吵不醒他们,待他们睁开眼睛,往往都日上三竿了。
1942年2月的最后一天,厄运落到南京水西门日籍华人富商王雨岩头上。王富商是江苏泰州人氏,其父做过清廷的官员,民国后家道败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还能去日本留学,学的是当时中国赴日留学生的冷门专业——贸易。王门祖上没人做过生意,可这王雨岩却不知怎么的,对贸易学特别有感觉,成绩优异就不必说了,难得的是,只要是与贸易相关的科目,他学起来一点儿不费劲儿,其超常的理解力和举一反三的水平,往往让那些挑剔的东洋教授都赞不绝口。
日本人精乖,王桑还没毕业,校方代表就找他谈话,请他签约留校担任助教。没毕业没关系,毕业证书的给!不想留校也可以,去经济省的干活,那边对你大大的欢迎!
王雨岩真的就去了经济省。那边二话不说,先让他加入了日本国籍,他自己起了个日本名字叫大本三郎。上司还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是正宗日本人,当时还是大学生。王雨岩到经济省上班后,人家让他分管对外贸易中与中国经贸往来的指导工作,名曰“顾问”,只管指手画脚,实权寸无。好在收入不错,相对于国内同类职位算是高薪了,王雨岩很满足。
这一干,就是十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各部门要把开支压缩下来支援军队,最好的方式就是开革公务员。王桑虽是日本国籍,依然属于边缘人群,在首批开革之列。其时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蔓延,王雨岩走到哪里,都是白眼相待,自感无趣。他婚后未有子女,两年前妻子患肺结核医治无效而殁,从此无牵无挂,遂有了回中国的想法。
就在这时,未婚的小姨子小田谷子突然提出要嫁给姐夫做填房,和他一起去中国定居。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王雨岩遂携新妻坐船出发,于上海沦陷后的第三天抵达,先在法租界混了半年,又去了南京。
这主儿的商业头脑实在不错,到南京后,用自己历年的积蓄加上小田谷子的私房钱开了一家门前高悬太阳旗的洋行,经营的产品只有一样——舶来品避孕套,而且只做批发生意,谢绝零售。南京地面上的老百姓都说这王汉奸疯了,什么生意不好做,竟挑这一门着手。王雨岩从前的中国朋友中也有些没民族气节的,上赶着过来巴结。提及避孕套生意,王雨岩说日本陆军部正在起草文件,要求在华部队必须“适当配备”避孕套,两个用项:防止性病以及特种军事用途。
前一项好理解,这后一项,那些老同学就不懂了,避孕套还有军事用途?王雨岩冷笑:“你们中国人这种脑子,只配做亡国奴。告诉你们,大日本皇军在中国征战,许多地区到处尘土飞扬,对于士兵枪支的保养徒增麻烦。因此,大日本陆军部的专家想出了一个简单有效而且经济的对策——行军时用避孕套罩住枪口,这不就把沙尘给挡住了?而且不妨碍紧急状况出现时的快速反应,要使用武器,顺手一撸不就给撸下来了。就算不撸也没啥,直接勾扳机就是,子弹照样出膛嘛。”稍后的情况还真如王雨岩所说,他这家洋行的避孕套批发生意特别兴隆,轻而易举就赚了个盆满钵溢。
王雨岩虽然在朋友面前趾高气扬,其实也有自知之明。他是日本国籍不假,但他心里清楚,在老百姓眼中,他依然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像他这样的料,别说在战争期间了,就是中日战前,也是不受国人待见的对象。这当儿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还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但凡是个有点儿血性的中国人,都恨不得吃小日本的肉,喝小日本的血。尽管他自认为其所作所为并没有得罪到具体哪个人,只不过做个避孕套的生意嘛,但肯定有人对他的项上之物感兴趣,故而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极为在意,不但把住所迁到了治安有基本保障的南京市区北侧,取名“静修阁”,还雇请了四名保镖,其中两人是日本人,家里的下人也是从泰州老家找来的。如此严密的保护措施,他的性命倒是无虞,却被江洋大盗盯上了。
却说1942年2月28日晚上,那个纵横江湖十六年一直毫发无损的“无形一炷香”采用开锁手段从后门进了“静修阁”。“静修阁”既有中外保镖,又有日本狼狗,外加触发式警报装置,戒备森严,“无形一炷香”不敢有半点儿疏忽,事前多次踩点,将其内部情况摸得八九不离十了,才制定了作案计划。
首先用毒饵解决了狼狗,继而用迷魂香熏倒了前院值班的两个中国保镖,想想还不放心,又潜入后院,在轮班休息的两个日本保镖的宿舍里点了支香,确认四人都失去了意识,这才潜入二楼王雨岩卧室,将王熏昏后下手行窃。据汪伪警察局办案刑警的统计,“无形一炷香”这次收获颇丰,窃得的金器、珠宝、美钞折合黄金在百两以上。
这也是“无形一炷香”此生的最后一案。说来难以置信,终结了这个黑道高手的竟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东洋女子——由王雨岩的小姨子升级为填房的小田谷子。
王雨岩压根儿就不知道,他的第二任妻子竟然是日本特务。当初他在日本被经济省开革,被迫狼狈赴华,其实是日本特务机关一手策划的,为的是让小田谷子前往中国进行特务活动有一个令外界信服的理由。
说到小田谷子的具体任务,就不得不提到日本陆军部所辖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部门——“陆字05室”,该室的主要职能就是对日本陆军派遣在外的所有特务机关的活动进行秘密监察。
中学还没毕业,小田谷子就被军方物色作为特工培养,接受一系列正规特务训练后,先是被派遣到台湾),学习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后又被派遣到澳门、香港“实习”, 经考核成绩优秀,晋升为陆军少尉,然后就在特务机关的安排下嫁给王雨岩,随夫赴华进行秘密工作。小田谷子的这番经历,连其枕边人王雨岩都浑然不知,更何况“无形一炷香”,否则,也不敢去动王雨岩的脑筋了。
“无形一炷香”在“静修阁”搜刮了一番,照例消除了所有的痕迹,在客厅的墙上留下一行江南六城警方早已熟悉的墨迹“无形一炷香到此一游”之后从容而去。前脚刚离开,后脚小田谷子就回来了,这绝对是一个计划外事件,使得原本要到天亮后才被发现的盗窃案提前暴露,最终导致“无形一炷香”折戟沉沙。
事先小田谷子对丈夫说,她要外出参加一个夜宴活动,活动的举办者是日本华东派遣军第十三军师团参谋长松本少将,而松本少将的夫人是小田谷子的闺蜜。以往这种情况,小田谷子肯定要和闺蜜聊个通宵,当晚就住在闺蜜家,不料那天松本夫人突然身体不适,夜宴活动不得不提前结束。
小田谷子回家一看,自是震惊。也顾不上对丈夫等一干被熏昏者施救,先取出秘藏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向“陆字05室”驻上海的秘密据点拍发急电报告此事。这倒不是心疼自家遭窃,急着追回损失。小田谷子也算是资深特工了,面对这种情况,她首先想到的是:“此举是不是哪个特务机关所为?我的秘密身份是不是被人察觉了?”
那么,发过电报,就该去救治丈夫了吧?没有。如果她存着这份念头,就不会被“陆字05室”选中了。她在家里各处转了一圈,查看自己的秘密是否有暴露的可能。之前小田谷子在一些关键地方撒下了特工专用的细粉,一旦有人经过就会留下痕迹。“无形一炷香”再厉害,也斗不过职业特工。于是,十六年来一直未在现场留下过任何蛛丝马迹的江南黑道高手,终于遭遇了滑铁卢。
“陆字05室”把这些信息转给了军方,案发第二天,南京日军宪兵队特高课接管此案,“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和汪伪“首都警察厅”奉命协助。
一星期后,日伪特务和警探追踪到芜湖,在市郊一座尼姑庵里找到了在此带发修行的女居士穆夫人。不过,他们未能将其生擒活捉。这位江南黑道高人听见前院喧哗、尼姑庵四周犬吠频起,就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当场服毒自尽。待一干特务闯入后院,她已经气绝身亡.…
说了半天,江洋大盗“无形一炷香”和此刻裴云飞、张伯仁调查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呢?关系还真不小。这起交通肇事案的死者袁维珍,就是“无形一炷香”的亲传弟子,此女真名殷千媚,师父还给她取了个匪号,曰“一枝花”。
四、漏网女弟子
这位神秘的穆夫人一共收了四个弟子,均为女性。她本人隐居芜湖尼姑庵,四个女弟子则分别居住于上海、杭州、南京和苏州。她每年分赴江南六城作案,女弟子们一般都要提供助力,诸如事前踩点,事后提供安全处所帮师父藏身之类。
穆夫人自尽后,日伪警特把尼姑庵挖地三尺,却没搜得任何财物。他们当然不会就此罢手。尼姑庵的住持说,穆夫人是两天前回来的,说是去上海探望亲友了。可她作为礼品送给住持的诸如枣泥麻饼、玫瑰酥糖和上好的碧螺春茶叶,却都是苏州特产,日伪警特遂把苏州纳入了侦查视线。
通过对那些出售土特产店铺的调查,日伪警特锁定了穆夫人在苏州落脚的旅店,继而从旅店方面获知,为穆夫人订房间的是一个何等长相的年轻女子,穆夫人在旅店居住期间,这个女子还多次来拜访。又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把该女子抓获。她就是穆夫人的小弟子唐洁芳。
唐洁芳被捕后,供出了她的三个师姐——上海的大师姐“一枝花”殷千媚、杭州的二师姐康菊芯、南京的三师姐黎赛翠。康、黎两人随即落网,而“一枝花”殷千媚在上海的住址三个师妹均不知晓,故而未能顺藤摸瓜一并擒获。
日伪警特根据被捕三女的口供分析,穆夫人在南京实施对“静修阁”的作案后,应是先去了上海,在沪上盘桓了数日,又去了杭州,然后才到苏州。其南京弟子黎赛翠供述,师父以往赴南京,都下榻于她家,这次却并未提前知会,她根本不知道师父来南京了。听说“静修阁”遭“无形一炷香”光顾,她大吃一惊,不知师父这次为何不跟她联系。
康菊芯供称,穆夫人来杭州后,并未去她家,而是在外面给她打了个电话,约她在“奎元馆”见面。当晚,师徒俩在“奎元馆”的一间小包房里吃了顿饭。席间穆夫人说,这可能是师徒俩的最后一面了。康菊芯暗暗心惊,忙问何故。穆夫人告诉徒弟,近日她在南京干了一票,照例马到成功。但不知怎么,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康菊芯心存侥幸,宽慰师父:“师父您吉人天相,不会有事的。”
穆夫人长叹:“有没有事,要看命数。我当时就卜了一卦,大凶……出道以来,从没有过这种卦象,看来这回是要翻船了。离开南京后,我去了上海你师姐千媚那里,刚才对你说的话,我也对她说了。我给你们师姐妹留下了一点儿东西,暂时放在千媚那里。无事便罢,一旦我出了什么事,她自会召集你们去上海,那些东西,你们姐妹分了,日后安身立命,都有个好归宿。”康菊芯当即哭拜,伏地三叩首。待她抬起头来,穆夫人已经飘然而去。
其后,穆夫人又去了苏州,对唐洁芳也作了一番类似的交代。她还告诉唐,在南京作案前,她就隐隐有不祥的预感,故而没有跟黎赛翠见面。此次来苏州,她没像以往那样住在唐洁芳家里,而是选择住旅店,也是这个缘故。
于是,日伪警特在上海全市布下天罗地网,搜捕殷千媚。其时已是1942年3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沪上租界,孤岛时期结束,整个上海都被日军控制。但上海毕竟是个国际大都市,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行踪不定、无人了解其底细的江洋大盗的弟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伪警局奉命抽调精干刑警组建“专案协办组”,当时在刑侦大队当差的张伯仁也被选了进去。为抓捕殷千媚,沪、宁两地的日伪警特一共出动了上百人,从1942年3月中旬开始,一直忙活了四个多月,最后依然两手空空。
到了这年7月底,从南京那边过来侦办案件的警特撤回去了,上海伪警局的“专案协办组”也就地解散。从此,“无形一炷香”的这个漏网女弟子“一枝花”就再也没有音信了。不过,张伯仁等一干刑警闲来无事,喝酒饮茶瞎唠嗑时还经常提到她,都认为这个女盗应该还在上海,当然,肯定是改名换姓洗白身份了。手里的赃款赃物,够她花一辈子了,她若是识时务,应该再也不会露面了。
老刑警张伯仁说到这里,不由感慨:“都是定数啊,这个‘一枝花’竟然躲在甜爱路,就这么让一辆轿车给撞死了……”
裴云飞先前听张伯仁说到“一枝花”,就感觉有点儿耳熟,待对方说到“无形一炷香”,立刻想起自己的授业恩师“江南神锁”窦老大讲述江湖掌故时,曾提及这个名号。但窦师父感兴趣的是此人的开锁技艺,没交代这个江洋大盗的最后结局,甚至也没说明此人的性别。倒是说起过“无形一炷香”有四个弟子,其中大弟子“一枝花”是得其真传的。
另外,裴云飞记得师父还说过,“无形一炷香”的开锁技艺可能跟自己同出一脉,具有开锁速度快疾、手法干脆利落、工具五花八门的特点。怪不得当时看到白铜匣子里那套开锁工具,他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尤其是那串精钢钩子,不但跟窦师父传给自己的那套形制相似,而且还多出十几枚。
当然,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裴云飞的思路很快回到案子上,他递给张伯仁一支香烟:“老张,你刚才说的这些,是从哪里得知的?”
张伯仁说:“我看过南京王宅案子的赃物清单,清单上列出的首饰,不少来自南京八大银楼之一‘梁永泉金店’。刚才那个铜匣里的金器,也有不少打着‘梁永泉’的印记。还有就是那支勃朗宁手枪,跟赃物清单上的枪号一模一样。所以我才推断,那个被轿车撞死的女子就是‘一枝花’。至于‘无形一炷香’那个案子的情况,都是该案撤销后跟刑队的弟兄闲聊时听说的。按咱们这行的规矩,敏感话题要么不谈,只要说了,应该都是实情。”
裴云飞觉得对方此言不谬:“这样看来,咱俩为调查袁维珍车祸致死案,误打误撞翻出了十年前的旧账。这事往下怎么办,还得请示领导。我在这里守着,辛苦你再跑一趟,往分局打个电话,要是刑队领导不在,就直接向郁局长汇报,请求派员过来保护现场,检点这些财物。”
可以想象,往下裴、张一老一少光是汇报情况,制作清单,起草带现场勘查图的书面报告就得忙一阵了。待完成这些工作走出分局大门时,外滩的海关大钟正好敲响十二下。
第二天上班后,郁局长把他叫到局务会议上,让他谈谈工作思路。他建议去南京老虎桥监狱外调,寻找穆夫人其余三个弟子的下落,让她们辨认照片,看袁维珍是不是她们的大师姐,如果是,可以向她们了解相关情况,从中寻找线索。与会领导均表示赞同,郁局长当场批了条子,让他去财务股领差旅费,和张伯仁一起前往南京。
五、“逍遥阁”的“清倌人”
裴云飞、张伯仁两人这趟差一出就是五天。他们认为,穆夫人那三个女弟子当初既然是被日伪南京警方逮捕的,也该由日伪南京地方法院审判。估计三女罪不该死,判处有期徒刑后押解南京当地唯一有女监的老虎桥监狱服刑。至今已时隔十年,如果她们还在服刑那最省事,若是被释放了,监狱方面也该知道她们的去向。来到老虎桥监狱一打听,得知这三个女贼是在1942年4月被日伪南京地方法院判的刑,二弟子康菊芯领刑十二年,三弟子黎赛翠十年,四弟子唐洁芳八年六个月。其中康菊芯在老虎桥监狱服刑两年多,于抗战胜利后被其家属托关系移押老家杭州的监狱服刑了;唐洁芳于1950年11月刑满回了苏州;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监狱系统,黎赛翠在老虎桥继续服刑,因表现较好,于去年9月23日提前获释。
两刑警根据老虎桥监狱提供的地址找到黎赛翠,拿出袁维珍的照片请她辨认。黎赛翠一眼认出,照片上的人就是殷千媚,还说这个大师姐长相甜美,江湖人称“一枝花”。至此,袁维珍就是“一枝花”的判断终于得到了证实。
但往下,这位师妹就提供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情况了,不但不清楚她住在上海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她跟着穆夫人或单独作过些什么案子。穆夫人的反侦查意识非常到位,在四地各收一个徒弟,未经她的允许,师姐妹之间不能私自见面。即便是召集徒弟相聚,也尽量避开芜湖、上海、南京、杭州、苏州这几个城市,相聚的日期由其分别通知。有时师父不打招呼,突然出现在某个徒弟所在的城市,其目的或是带徒弟在当地作案,或是知会一些长三角地区警方的反盗动向之类的情况。
此时距穆夫人自裁已有十年,黎赛翠提及这个黑道师父时,语气仍旧恭恭敬敬,由此可见这个“无形一炷香”的厉害。
裴云飞、张伯仁商量了一下,认为有必要去南京市公安局调阅日伪“首都警察厅”留下的关于王雨岩宅被盗案的刑事档案,也许能够获得些许线索。可他们的指望落空了,日伪旧档案中有关此案的记录没有超出张伯仁了解的范围,至于其他鸡毛蒜皮的细节,也跟他们要调查的“一枝花”不沾边。
隔天,两人去苏州,接着又赶到杭州,见到了唐洁芳、康菊芯。这二位,前者嫁给了一个开茶叶店的老板,已经生了孩子,后者则在杭州郊外的一个尼姑庵里出家了。考虑到保护她们的隐私,两刑警是在当地公安局的安排下和她们秘密见的面。此举让她们颇为感动,都愿意为刑警的调查提供协助,可她们所说的情况跟黎赛翠一般无二。当然,这两位女性都保持着职业黑道超强的眼力,尽管时隔十年,还是在第一时间准确无误地认出了照片上的大师姐。
返沪途中,裴云飞、张伯仁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既然袁维珍的三位师妹提供不出有价值的线索,那就必须重新开辟一条调查之路。裴云飞提议:“要不咱们去袁维珍生前的‘工作单位’了解一下情况?”
回到上海已过中午,两人直接去分局销差,在单位食堂对付了几口冷菜残羹,便直奔四马路的“逍遥阁”。
让两位刑警庆幸的是,这趟终于没有白跑。
“逍遥阁”是四马路上一家论经营时间可以进入前六名的老字号。
1900 年闹义和团那会儿,从京城逃出来的难民中有一个出身于没落旗人家庭的中年女子关氏。她带着八岁女儿一路南下,辗转一个多月才来到上海。原本打算投靠一个早年来沪上跟洋人合伙做生意的亲戚,不想母女俩千辛万苦找到其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寓所时,这位亲戚刚刚因病医治无效咽气了。好在这个发迹买办不是忘恩负义之徒,直到临终前还在念叨着关氏已故丈夫生前对他们全家的关照,向私人律师口授遗嘱,命全体在场家眷签字,自己挣扎着在上面按了一枚指印,给关氏留下了一笔银洋。
关氏的已故丈夫曾在北京入股与人合伙开过妓院,虽然并不直接参与经营,但关氏整日价听到的都是这类话题,对于行院多少是有些了解的。她在上海落脚后,就用买办亲戚给她留下的这笔赠款和另外一个逃难旗人合伙开了“逍遥阁”。
关氏人很聪明,情商也不低,而且出身武官家庭,丈夫也当过清军的下级军官,因而自带一股豪迈气质。几年下来,她把上海滩那些地痞流氓、租界巡捕笼络得很是到位,“逍遥阁”的生意说不上多好,但也能经营下去,在同行业中处于中等水平。一晃儿二十年过去,关氏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把已经独资的“逍遥阁”留给了女儿富翠儿——关氏的夫家是富察氏,待清帝退位、民国成立,遂改姓富。
富翠儿十八岁上嫁了个工厂小开,小两口原本过得不错,不料结婚才两年多,丈夫遭遇横祸,租界流氓打群架时他正好路过,避让不及,竟在混乱中让人给砍死了。夫家原本就对这个儿媳的家庭出身不满,只因那小开恋着人家要死要活非富翠儿不娶,才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如今小开一死,夫家便将其扫地出门。
富翠儿回到母亲身边,不想参与行院管理,就去公共租界的一家洋行找了份打杂的工作。富翠儿长得有几分姿色,待人接物懂得进退,处事周全得当。时间稍长,被经常来洋行的老板小舅子、供职于巡捕房的英国技术警官威廉看中,娶其为妻。可惜好景不长,威廉奉派出差,不幸感染霍乱,救治无效,一命呜呼。
富翠儿人生中第二次以寡妇身份回到了“逍遥阁”,其时她只有二十六岁。这回她认命了,断了再嫁的念头,跟母亲学习打理行院。其母病逝后,富翠儿接手“逍遥阁”,打出了一套令沪上烟花行业大跌眼镜的组合拳——
先是裁减人员,不管以前在其母手里立下的是死契还是活契(死契系妓女人院时买断终身,生死由命,打死勿论,如要从良嫁人,须向老鸨交纳一笔钱钞;活契类似雇佣合同,老鸨不得随意打骂,但可以按照行规予以经济制裁,若要提前离开,那就得承担“违约责任”),只要想离开的,可以任意走路,无须承担所谓的“违约金”。
再是把“逍遥阁”的所有男性从业人员即北方称为“大茶壶”的杂役兼保镖以及厨子全部辞退,改聘女性。那么,如果有人来“逍遥阁”闹事该怎么办?这个,富翠儿袖中另有乾坤:她有母亲及第二任丈夫生前留下的巡捕房和帮会人脉,而且她聘任的女性员工,不但具有帮会背景,体格也类似北地著名的“三河老妈子”,还都会些三脚猫拳脚功夫。
还有第三,就是将“逍遥阁”提高档次,扩大经营范围,登报招聘“清倌人”。所谓“清倌人”,就是指只卖艺、不卖身的青楼从业女子,不但相貌清丽脱俗,还精通吟诗作对、琴棋书画等才艺。
富翠儿的这套组合拳打出来,一时间,“逍遥阁”顾客盈门,预约不断,有的甚至要等到一个月之后。加之富翠儿跟警方和帮会的关系,给人一种安全感,沪上甚至外埠一些“清倌人”纷纷跳槽“逍遥阁”,投到富翠儿门下。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并非职业“清倌人”,但由于各种原因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前来应聘,已经易名袁维珍的殷千媚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上海解放后,“逍遥阁”的生意就一落千丈了。裴云飞、张伯仁前去调查时,“逍遥阁”尚未关闭,但已经是门可罗雀。该行院于本案发生后的次年关门歇业,富翠儿之后创办了一家私立幼儿园,1958年幼儿园转为公办,富氏退休,返回北方原籍地,不知所终。
富翠儿告诉前来调查的刑警,袁维珍未曾报名预约,而是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突然登门求见。当时她自报二十岁,南京人氏,以前未曾从事过青楼行业,对其也不了解,因家中发生变故,不得已离家出走来到上海。赴沪途中,买了份《申报》消磨时间,在报上看到了“逍遥阁”的广告,对“清倌人”职业产生了兴趣,比照广告所列条件,自认为合适,就有了登门造访之念。
以富翠儿的江湖经验,马上意识到这姑娘不是寻常女子,从其表现出的那份明显超出年龄的从容老到,即使以“不寻常”的标准来衡量,也绝非凡品。富翠儿估计,这女子多半是道上角色,是个有故事的人。
富翠儿的性格跟其母相似,骨子里具有“冒险基因”,如果搁在当今,没准儿就是“翼装飞行”、“低空跳伞”等生命极限运动的热衷参与者。体现在这件事上,就是迅速作出决定:啥都别问,先把她收下再说!如此,袁维珍这个正被日伪警方通缉的黑道美女,就成为“逍遥阁”的一名“清倌人”,殷千媚这个名字以及当初师父穆夫人给她取的“一枝花”匪号,从此彻底湮灭了。
一段时间下来,富翠儿觉得自己的眼光不错。袁维珍虽然从未接触过“清倌人”这门职业,但她非常聪明,“清倌人”的诸般应知应会,跟她一说就明白。吟诗唱曲、弹奏乐器她原本就在行,舞蹈绘画没接触过,不过,经富翠儿请来的师傅调教,由于其超常的悟性加上肯下功夫,进展惊人。
本来照这势头,袁维珍成为“逍遥阁”的翘楚不成问题,毕竟“清倌人”的才艺仅仅是吸引客人的手段,并不需要达到专业艺术标准。可袁维珍自己却并不愿意出名,当然,她从来不曾跟富翠儿当面表示过。
袁维珍每当发现自己即将进入“逍遥阁”预约榜前三名时,就向老板富翠儿请假,时间有长有短,少则三天,多则七八天,最长时有过半个月的。至于影响收入,袁维珍根本不在乎。
时间一长,富翠儿更加怀疑袁维珍系警方通缉对象,就产生了弄个明白的念头。倒并非故意跟袁小姐过不去,也不是担心万一被捕牵连“逍遥阁”,凭她跟警方的关系,这点儿小事还是能摆平的。
富翠儿的第二任丈夫,也即那个巡捕房的英籍警官生前有个要好的同事,上海沦陷后转而为日伪警察局效力。大约在1944年春,富翠儿请其相帮打听最近几年(重点是1942年前后)外埠警方通缉的有可能潜藏在上海的女性逃犯的情况。此人的办事效率相当高,也就不过三天时间,富翠儿就拿到了六份外埠警方发至日伪上海警察局的协查通报,其中五份有照片,一看就知不是袁维珍;还有一份由日伪南京“首都警察厅”发出的协查通报没有照片,但其文字描述与袁维珍酷似。
富翠儿恍然,原来这位袁小姐乃是曾在江南黑道上赫赫有名的大盗“无形一炷香”穆夫人的弟子“一枝花”,不由暗自庆幸没亏待过人家,否则像袁小姐这样的角色,哪天要想跟她富老板过不去的话,对“逍遥阁”来个放火投毒,抑或施展本门手段将贵重细软席卷而空,那还不是轻而易举?从此,富翠儿与袁维珍心照不宣,相安无事地维持东伙关系,彻底断了靠袁小姐让“逍遥阁”在沪上青楼行院扬名立万的念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政权提倡新风气,“逍遥阁”的生意逐渐清淡,登门来会“清倌人”的主顾更是日渐减少。1950年初秋,袁维珍向富翠儿提出离开“逍遥阁”。怕富翠儿误会,她特意说明,并非是想另谋高就,而是不打算再从事“清倌人”这份职业了。好聚好散,富翠儿自不会难为她,更不提什么“违约金”。袁维珍也很领情,在四川北路“泰山饭馆”请富翠儿吃了一顿分手饭。饭后,又邀富翠儿去附近她的住所喝咖啡。直到这时,富翠儿才知道袁维珍住在甜爱路。此后,富翠儿再也没跟袁维珍见过面,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联系过。
尽管富翠儿和袁维珍打了多年交道,对她的了解其实有限得很,甚至提供不出和袁维珍交往稍微密切些的同事或顾客,裴云飞多少有点儿失望。张伯仁却正相反,毕竟是老刑警,经验丰富,这时他已经有了点儿想法。他向富翠儿打听:“你那次去甜爱路袁小姐府上,在她家里见过什么值钱又便于隐蔽携带的财物吗?”
富翠儿说:“像袁小姐这样的人,金银珠宝自然少不了的,但她不可能拿出来给我看……哦,我想起来了,要说值钱的东西,她有一架德国蔡司照相机!当时她还说,这相机有自拍功能,要和我拍一张合影,好留个念想。可是,相机里的胶卷用光了,那就拍不成了。她说改日备好新胶卷,就去‘逍遥阁’找我。想来只是一句客套话吧,反正她后来再也没去过‘逍遥阁’……”
两个刑警对视一眼:在查看袁维珍甜爱路的住所时,并没有发现这样一架照相机。是袁维珍生前处理掉了,还是被潜入其住所的不速之客给顺走了?
蔡司照相机是德国名牌,哪怕是多年前的旧货,也能卖出相当高的价格。裴云飞、张伯仁商议片刻,决定去中央商场碰碰运气,打听一下这几天是否有人出手这么一架照相机。说不定,这架蔡司照相机可以成为此案的突破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