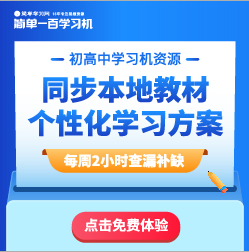那次回家,陪母亲在村里散步,看到池塘边一个豁着耳的石磨被用作洗衣石,石磨露出水面的部分浅埋在发硬的泥土里,水中的部分长满了拖着长丝的青苔,我的思绪一下涌入到了童年的磨房里……
1965年秋,父母携奶奶、大姐二姐、我及两个妹妹全家八口人从西安下放到现在的村上。童年的记忆里,村子很大,分南、北、东三个小村共有七个生产队,我家所在的南村二队大约有七八眼石磨,合六七户人家一眼。由于人口多,石磨很少被闲置。我们无磨的人家要提早去磨主家排队“问磨”,一般在“问磨”后的第二或第三天才能轮上。
村上的磨房大多为配房,粘土墙麦秸顶,屋檐下,一扇小得可怜的窗户透着柔弱的光。
石磨最受乡亲们的宠爱,它墩实、凝重、不分昼夜不辞辛劳地转动,它那连接磨棍的磨耳绳始终绷得紧紧的,两只磨眼喉咙般将粗糙的粮食咽下,“轰隆隆”的磨声和着房前河里的流水声时而奔涌,时而迂回,不知疲倦地奏响着生命的交响曲。磨磨薄了,身体变小了,将竭尽全力磨出的粉奉献给苦涩岁月中的乡亲们。
石磨用力地咬嚼着小麦、玉米、高粱及碎山芋干与黄豆混合的粮食,牙齿逐渐变钝,直至用牙床嘬动,虽然推起来明显见轻,但磨粉效率明显下降,原本磨五遍的现在需要磨上七遍。此时,走乡串户的锻磨匠肩搭汗巾,手握錾子挥着铁锤,对着石磨咬合面上的“人”字型齿槽一锤连着一锤,石屑崩溅,火花闪现。
经过锻凿的石磨陡然来了精神,牙齿锋利,咬嚼粮食的声音突然变得清脆,悠悠岁月中还有比这更沁人肺腑的声音吗?
农闲时,生产队的驴子被各家轮流牵去拉磨。轮上我们家时,我就兴奋地蹦跳着来到牲口屋门前,掀起门上的保温草珊,习惯性地抓住那扇破旧木门上的铁钌铞晃几下,示意值夜班的饲养员伯伯我要牵驴子拉磨去了。
驴舍两侧的青石槽里,铡碎的干草与豆饲料混合成的驴食已所剩无几,一头驴用舌头舔着光滑锃亮的槽床,我抬手正欲解开系在横棍上的缰绳,趁我不备,驴子紧绷着下嘴唇卷起上嘴唇,露出它那排硕大的板牙,连续抖动着嘴打出一个喷嚏,喷出的黏液溅在我脸上,我下意识的抬起膀子,用发硬发亮的黑粗布棉袄袖子在脸上蹭几下,隐约感到那令我作呕的黏液里还散发着豆饲料的余香味儿。
驴拉磨的套具被乡亲们称作驴耕:上下端以细绳相连结的两根木棍呈“八”字型夹在驴的脖子上,夹棍中部系着的两根较粗的拉绳栓在驴身后的磨棍上,驴一使劲,拉绳深深勒进身子两侧最突出的部位。
我将挂在墙上的驴耕取下来,踮着脚搭在驴身上,牵着驴快速向磨房走去。
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大姐和二姐从家里挎着盛满粮食的笆斗子就直奔磨房了,驴拉磨是我们身心倍感轻松的时候。
磨房土窗台上的黑瓷碗里,一根棉制灯芯从棉油里爬上碗边昂着头,挑着的柔弱的橘黄色火苗不安分地扭动着。
开磨前,要打扫磨道,在架案上支筛粉笸篮,往磨顶上粮食,绑扎磨棍,整理耕绳套上驴,一切准备就绪,太阳已悬在树梢。
阳光从木窗的格栅里照进来斑驳地落在母亲身上 ,驴子习惯地折回头啃两下肩膀,还不时地抬起后蹄在肚子上蹭几下,母亲见状,会意地弯下腰,四指并拢蜷曲,在驴子浑圆的肚子上,尽心尽力地耕耘着驴毛。母亲还不停地招呼我离远些,被扬起的乳毛和灰尘在窗户射进来的光束中游荡,附着在母亲的脸上,钻入她的鼻孔和耳朵里,母亲用缝里卡着驴毛的指甲轻轻在自己脸上挠几下。面粉的余香味、驴粪尿的腥臊味、棉油灯散发出的香中带苦的糊味与淡淡的土墙味儿混合在磨房里。
我手挥着藤条,不时地吆喝几声,被蒙着眼的驴子就乖乖地在磨道里一圈圈走起来,当石磨顶部粮食漏成漏斗状时,我们便把边上的粮食往磨眼上堆,遇驴屎蛋落磨道也是要及时清扫至外围的,否则会让人苦不堪言。若是我们开小差,驴子有时就会偷懒停下来,甚至伸嘴偷食磨盘上的粉。磨顶的粮食经磨眼漏向上下带齿的咬合面,随着上半部转动,被辗成的粉雨帘般地挂满了石磨一周。笸篮里支起由两根扁竹作滑轨的箩床,姐姐侧着身子弯着腰跟在驴子后面,左手抓着葫芦开成的面瓢,右手快速灵巧地将磨盘上的碎粉涌进瓢里,倒在筛箩内,在箩床上拉锯式住复筛动,面粉下雪似地也落在笸篮里,母亲不时用手摊推着逐渐堆高的面粉。如此将粮食磨上五六遍,粉几乎全被磨出,只剩下麸子即算完成。
牲口中只有驴子是适用拉磨的,过年或冬闲之外的时光,生产队要将驴子用于耕田耙地拉大车,我们享受驴拉磨的日子一晃即逝。
平常吃面主要靠人力推磨,推磨是力气活。推磨时,外侧的手扶着横在腹部的磨棍一圈一圈使劲往前推,内侧的手不时地往磨眼上堆着粮食,每一次磨四五十斤粮食需要耗去两个多小时,手握磨棍迈着沉重的步伐,转着数也数不完的圈,憧景着驴子拉磨的日子。
小时候,常常看着大姐二姐在母亲的吆喝下,就着昏暗的棉油灯光,下穿肥大的蓝色土布裤,上着盘扣置于腋下的碎花大襟衣,头顶蓝白相间的条纹粗布巾,在面粉弥漫的磨房里推磨过筛,身上落一层浅霜般的浮粉,把生命的张力发挥得淋漓尽致。隆隆的磨声记录着我童年磨房时光的每一个足迹。
那年月粮食紧张,入秋后就很难吃到细粮,在漫长的冬季我们要节衣缩食,省下点粮食,为的是能熬过那青黄不接的时节。在没有粮食可食时,就将喂猪的纯山芋干碾碎后再拿来磨成粉,拌和着各种野菜蒸成窝窝头。有时作业完成后,跑去磨房和父母姐姐一起推磨,那石磨确实太重,我年龄小开始还有点力气,不久就累得头晕眼花瘫软下来,母亲瞧着心里不忍,就让我到磨房外的石凳上休息。
峥嵘岁月里,石磨转走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磨砺了大姐二姐的青春年华,蹉跎了我父亲母亲中年时光。
村上人沿袭着先人用石磨磨粉方式,一辈辈一年年,石磨的牙齿磨钝了,石匠再给它锻凿出新痕,磨绳拉断了,添加些蔴丝再搓上,我们腰背推驼了,父母脸上毅力纹也增多了。
无情的时光更迭让石磨惨遭淘汰,周边的宅基地在推土机“轰隆隆”的阵阵助威声中正蚕食着水塘,石磨静静斜躺在日见缩小的池塘边,恶臭的麦糠涌着腐朽的麦秸围拢着石磨;灰色水塘面上不时地冒出从塘底涌上来的沼气泡;歪斜着露出塘面的枯枝条上集满苍蝇;枝尽头挑着的千疮百孔的彩色垃圾袋在微风下颤动着,像是为石磨的葬礼准备的幡。
石磨不再被驴拉人推的昼夜忙碌转动,不会磨损也不会再遭锻磨匠的敲凿,浣衣女没了踪影,村姑村妇们的嬉戏、捣衣声早已淹没在了村史的尘埃中。
上个月赴桐城喝外甥女的喜酒,回头在三河镇逗留,走进一座农趣馆,院内四角钢管立柱的顶端连着红绸绳,拐角处设有一扇简易的贴着“福”字的便门,喜庆地将石磨围住,供游客购票怀旧、体验,看到它尊贵地矗立在院子中央欣喜地迎接着八方来客,方对水塘中命运多舛的石磨稍有释怀。
2016年6月20日(原载2016年7月13日新华网)